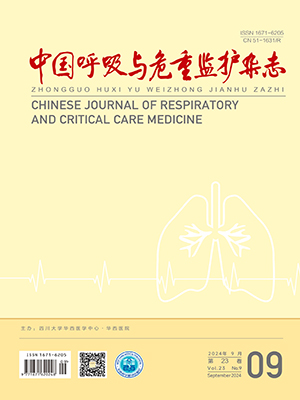引用本文: 刘玉, 张嘉瑞, 罗远明, 魏海龙, 葛慧青, 刘辉国, 张建初, 潘频华, 李先华, 周晖, 谢秀芳, 程丽娜, 易梦秋, 周宸, 阿地拉·艾力, 彭丽阁, 蒲佳琪, 刘亮, 张小红, 冯海沜, 周海霞, 易群.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合并社区获得性肺炎短期死亡及不良结局预测模型的验证研究.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3, 22(3): 159-167. doi: 10.7507/1671-6205.202301013 复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2019年的中国疾病负担结果显示,慢阻肺已居我国居民死亡病因的第3位 [1]。慢阻肺急性加重是慢阻肺患者住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住院死亡率可达7.52%[2]。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是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患者的常见合并症,研究提示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较单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不良结局明显增多,包括机械通气、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入住、住院时间延长、急性加重再入院及院内死亡等[3–8],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的住院患者进行早期准确的预后评估有利于指导治疗策略的选择及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并希望通过对高危患者的及时干预改善其预后。
目前,针对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和CAP患者均有一些预后预测模型,比如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常用的预后模型有BAP-65评分和DECAF评分,CAP患者常用的预后模型有CURB-65评分和肺炎严重程度评分(pneumonia severity index,PSI)。以上4种评分均在内部及外部验证队列中显示出良好的性能[9]。但是鉴于临床实践中,慢阻肺急性加重和CAP常合并存在,目前尚缺乏经过验证的适合这一人群的预后评估模型。本研究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的回顾性研究,评估和比较了BAP-65、CURB-65、DECAF和PSI 4种临床预后评分在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住院患者30天内死亡和不良结局方面的效能,并同时探讨了这类患者短期死亡的危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对象来源于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的一项全国、多中心的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患者的注册登记研究(简称MAGNET研究)。该注册登记研究前瞻性连续纳入了国内10 家大型综合三甲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乐山市人民医院、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2017年9月—2021年7月因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治疗的患者,收集患者入院时的基本情况、症状及体征、相关实验室检查及影像结果、治疗措施及预后等临床资料,并随访患者的预后。本研究从上述注册登记研究纳入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中筛选出合并CAP诊断的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慢阻肺急性加重和CAP的诊断经过两位经验丰富的临床专家复核。参照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21年修订版)》作为慢阻肺急性加重的诊断标准。CAP的诊断标准参照《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指南(2016版)》。研究对象入选标准为:① 因慢阻肺急性加重就诊的住院患者;② 同时符合CAP诊断标准;③ 年龄>40岁。排除标准:① 住院时间<48 h;② 缺乏入院后30天随访资料或临床资料不完整。本研究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分委会批准(2019年审1056号),并获得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编号:ChiCTR2100044625。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收集患者入院时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吸烟史等;合并症,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支气管扩张、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恶性肿瘤等;入院时的症状及体征,包括胸痛、呼吸困难、意识障碍、脉率、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呼吸频率等;相关实验室指标及影像结果(入院后首次结果),包括血红蛋白、白细胞计数、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心肌标志物、尿素氮、血气分析及胸部CT结果等;不良预后,包括30天内接受有创机械通气、入住ICU和全因死亡。
1.2.2 分组
将患者按照入院起至第30天是否死亡分为死亡组和生存组进行病例对照研究。比较两组患者入院时基础情况、合并症、相关辅助检查及预后等指标的差异。
1.2.3 预后预测模型评分
基于纳入的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入院时的临床资料,分别采用BAP-65、DECAF、CURB-65和PSI评分4种量表回顾性对患者进行评分及危险分级。 4种评分量表纳入的因素和评分标准如下。
(1)BAP-65评分包括血尿素氮≥7 mmol/L、意识状态改变、脉率≥109 次/min和年龄>65岁以上4个危险因素,根据年龄及风险因素分为Ⅰ~Ⅴ级,为便于模型间的比较,将Ⅰ~Ⅴ级分别赋予1~5分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
(2)DECAF评分包括呼吸困难程度、嗜酸性粒细胞减少(<0.05×109/L)、酸中毒(pH<7.3)、合并肺实变和心房颤动5个危险因素,DECAF评分中的呼吸困难程度采用扩展的英国医学委员会呼吸困难量表进行评价。呼吸困难根据程度赋予1分或2分,其余4项各为1分,其中,低风险为0~1分,中风险为2分,高风险为≥3分。
(3)CURB-65评分包括年龄≥65岁、意识错乱、收缩压<90 mm Hg(1 mm Hg=0.133 kPa)或舒张压<60 mm Hg、呼吸频率≥30次/min和血尿素氮>7 mmol/L共5个因素,每一个因素为1分,其中,低风险为0~1分,中风险为2分,高风险为≥3分。
(4)PSI评分有20个变量,包括人口学因素{年龄[男性,多少岁即多少分;女性,计为(年龄–10)分],护理院居住(10分)}、基础疾病[肿瘤(30分)、肝病(20分)、充血性心力衰竭(10分)、肾脏病(10分)、脑血管疾病(10分)]、异常体格检查[神志改变(20分)、呼吸≥30次/min(20分)、收缩压<90 mm Hg(20分)、体温<35 ℃或≥40 ℃(15分)、脉率≥125次/min(10分)]和辅助检查结果[pH<7.35(30分)、血尿素氮≥30 mg/dL(20分)、血清钠<130 mmol/L(20分)、血糖≥250 mg/dL(10分)、PaO2<60 mm Hg(10分)、血细胞比容<30%(10分)、胸腔积液(10分)]。根据得出的分数,分为Ⅰ~Ⅴ级,其中,Ⅰ、Ⅱ级为评分≤70分,但Ⅰ级的年龄<50岁且无基础疾病,Ⅲ级为71~90分,Ⅳ级为91~130分,Ⅴ级为>130分。
1.2.4 研究结局
主要研究结局是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的全因死亡。次要研究结局是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 30天内相关的总体不良结局,包括全因死亡、有创机械通气或入住ICU,发生上述三个不良结局中的任意一个及以上即定义为不良预后。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8.0统计软件。使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使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Q1,Q3)]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以例(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基于单因素分析结果,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死亡的可能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寻30天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值及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采用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来评估和比较四种量表预测短期死亡及总体不良结局的准确性,并分别计算4个量表的敏感性及特异性。采用Z检验两两比较4种量表的AUC。统计学检验为双尾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使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Q1,Q3)]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以例(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基于单因素分析结果,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死亡的可能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寻30天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值及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采用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来评估和比较四种量表预测短期死亡及总体不良结局的准确性,并分别计算4个量表的敏感性及特异性。采用Z检验两两比较4种量表的AUC。统计学检验为双尾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MAGNET研究共纳入了14007例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患者,其中3375例患者合并CAP诊断并符合纳入标准。纳入患者中男2545例,女830例,平均年龄(73.66±10.73)岁。入院30天内,129例患者发生死亡,614例患者发生不良结局,全因死亡率为3.82%,不良结局率为18.19%。
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死亡组患者的年龄为(81.39±8.94)岁,明显高于生存组[(73.35±10.68)岁,P<0.001]。在性别、体重指数、吸烟史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死亡组有意识状态改变的患者比例为41.1%,明显高于生存组(5.9%,P<0.001)。两组在呼吸困难、心悸、胸痛的发生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死亡组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房颤动、心力衰竭、慢性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生存组(均P<0.05)。两组在合并恶性肿瘤、肺栓塞、肝脏疾病的人数比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死亡组患者的脉率为(95.12±20.55)次/min,明显高于生存组的(89.85±16.60)次/min(P<0.05);死亡组患者的平均舒张压和动脉压分别为(68.43±16.02)mm Hg和(88.29±16.84)mm Hg,明显低于生存组[分别为(77.25±12.97)mm Hg和(95.19±13.50)mm Hg](均P<0.001)。两组患者在体温、呼吸频率、收缩压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死亡组患者的氧分压、白细胞计数、肌酐、尿素氮、合并胸腔积液的比例,明显高于生存组(均P<0.05)。死亡组患者的pH值、血红蛋白、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水平均明显低于生存组(均P<0.05)。两组患者在二氧化碳分压、血清钠、肺大疱的比例及CT显示右心室扩张的比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死亡组的中位住院时间为17 d,明显长于生存组(11 d,P<0.001);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率和ICU入住率分别为43.3%和42.6%,均明显高于生存组(7.3%,P<0.001;13.2%,P<0.001)。结果见表1。
 )/例(%)]
)/例(%)]
2.2 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中发现可能与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全因死亡相关的因素有:年龄、意识状态改变,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房颤动、心力衰竭、慢性肾病,脉率、舒张压、平均动脉压、pH值、氧分压、血红蛋白、白细胞计数、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血尿素氮、肌酐、白蛋白,合并胸腔积液,将以上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意识状态改变(OR=4.809,95%CI 2.931~7.889,P<0.001)、糖尿病(OR=2.052,95%CI 1.229~3.426,P=0.006)、心房颤动(OR=1.829,95%CI 1.020~3.281,P=0.043)、慢性肺源性心脏病(OR=1.644,95%CI 1.032~2.619,P=0.036 )、年龄(OR=1.075,95%CI 1.045~1.106,P<0.001)、脉率(OR=1.018,95%CI 1.005~1.031,P=0.006)、血清白蛋白(OR=0.946,95%CI 0.906~0.988,P=0.013)、舒张压(OR=0.942,95%CI 0.900~0.986,P=0.010)、pH值(OR=0.031,95%CI 0.001~0.656,P=0.026)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30天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见表2。
2.3 4种预后模型的预测效能比较
使用4种预后量表对纳入的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进行评分及死亡风险分级,结果见表3。ROC 曲线结果显示CURB-65评分、BAP-65评分、DECAF评分、PSI评分在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不良预后方面均有一定价值,预测全因死亡的AUC分别是0.780(95%CI 0.737~0.823)、0.782(95%CI 0.741~0.824)、0.614(95%CI 0.566~0.663)、0.816(95%CI 0.780~0.853),均P<0.001;预测总体不良结局的AUC分别是0.694(95%CI 0.669~0.719)、0.687(95%CI 0.663~0.712)、0.564(95%CI 0.539~0.590)、0.705(95%CI 0.682~0.728),均P<0.001(图1、图2及表4)。PSI评分对全因死亡及总体不良结局预测效能均最佳,DECAF评分最差。分别两两进行Z检验,结果提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1
4种量表预测30天内全因死亡的ROC 曲线
图1
4种量表预测30天内全因死亡的ROC 曲线
 图2
4种量表预测30天内不良结局的ROC曲线
图2
4种量表预测30天内不良结局的ROC曲线
3 讨论
国外文献报道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住院死亡率约为11%[5],本项在中国人群的研究发现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死亡率为3.82%,低于国外人群研究结果。另一项纳入1215例患者的中国研究显示,慢阻肺合并CAP的住院死亡率2.7%[10],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接近。国内外研究一致的发现是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短期死亡率明显高于单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5,10],比如MAGNET研究中单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死亡率为1.4%,而上述提到的另一项中国患者中进行的研究发现单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住院死亡率为0.9%[10]。这提示合并CAP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预后更差,临床实践中应尤其关注这类患者,早期准确评估其预后以指导治疗策略的选择。
意识状态改变、合并糖尿病、合并心房颤动、合并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老龄、脉率增快、血清白蛋白降低、舒张压降低、pH值降低在本研究中被证实为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的短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些研究发现基本与既往在慢阻肺急性加重或CAP患者中的文献报道一致[11–13]。另有研究认为心血管疾病[14]、嗜酸性粒细胞[15]、C反应蛋白[6]、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评分[6]是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死亡预测指标,即低舒张压,而收缩压与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的全因死亡无关。舒张压是临床容易测量的指标,既往研究证实低舒张压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风险[16–18],潜在的机制可能有如下两点:一是因为冠状动脉的血流供应主要来自于舒张期,心肌灌注严重依赖于舒张压,较低的舒张压可能导致心肌低灌注和相关的心肌损伤[19];二是大动脉弹性下降时,其大动脉的弹性储器作用减弱而降低舒张压,提示这些舒张压低的患者大动脉的僵硬程度更高,一般健康情况更差18。但是低舒张压增加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死亡风险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是否也是通过上述机制起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
BAP-65和DECAF评分是用于评估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预后的评估模型,CURB-65和PSI评分是用于评估CAP患者预后的评估模型。对于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人群,哪种预后评估模型更优尚没有一致的结论,且相关的研究也很少。我们的研究是第一个在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的住院患者中验证和比较BAP-65、DECAF、CURB-65和PSI评分准确性的大样本多中心研究。研究发现PSI评分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全因死亡及总体不良结局的效能最佳,而DECAF评分最差。PSI评分最开始被开发用于评价肺炎的严重程度,通过人口学因素、基础疾病、异常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结果等20个参数进行预后评价。有研究表明,PSI评分也可用于预测住院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住院死亡风险,且预后能力优于CURB-65和BAP-65评分[20],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的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全因死亡的可能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意识状态改变、脑血管疾病、心力衰竭、慢性肾病、脉率、pH值、氧分压、血尿素氮、胸腔积液,均包含在PSI评分的参数当中,其中年龄、意识状态改变、脉率、pH值是独立的危险因素。但PSI评分较其他评分相比较繁琐,操作复杂,且有些参数临床不易获取,如轻症患者可能不会进行血气分析检测等,一定程度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应用。既往的研究发现DECAF评分在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患者院内及早期死亡和对于低风险人群认定的准确性方面展示出良好的效能[21]。DECAF评分包括呼吸困难(D)、嗜酸性粒细胞减少(E)、肺实变(C)、酸中毒(A)和心房颤动(F)这 5 个易于临床获取的变量。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人群中其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早期死亡及总体不良结局的准确性较差。既往研究发现该评分虽然对低风险人群的认定有很好的准确性,但对于高风险人群的划分准确性较差,阳性似然比仅1.80[21]。预测效能较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该量表中呼吸困难的评估是基于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稳定期的状态,具有一定主观性,同时这种回忆性的评分也容易造成评分的不准确。
CURB-65及BAP-65评分分别用于CAP及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预后评估,二者纳入的指标很相似:CURB-65评分共5项指标,包括意识障碍,呼吸频率,收缩压或舒张压,年龄和血尿素氮,《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6年版)》[22]建议使用CURB-65评分作为判断CAP患者是否需要住院治疗的标准。BAP-65评分共4项指标,包括意识状态改变、脉率、年龄及血尿素氮,是由Tabak等[23]于2009年开发用于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使用机械通气的可能性及死亡风险的预后量表。这两种评分简单易操作,广泛应用于临床中,但是它们主要以年龄及生命体征作为评价标准,未结合更多的辅助检查项目,导致预测效能有一定局限性。不少研究显示,CURB-65评分及BAP-65评分对于慢阻肺急性加重和(或)CAP院内死亡[20-21, 24-25]或30天死亡[21]的预测效能较差,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的患者预后差,不良结局多。目前国内外有关上述4种评分对于包括有创机械通气、入住ICU、全因死亡在内的整体不良结局预测价值比较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结果尚存在争议。有研究显示,BAP-65比CURB-65更准确地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需要机械通气的风险,AUC分别为0.78比0.74[26];也有研究表明BAP-65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能力较差,AUC仅0.61[25]。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PSI、CURB-65及BAP-65评分对于不良结局都有不错的预测效果,其中PSI评分最佳;但DECAF评分预测效果较差。
综上,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死亡率及不良结局发生率较高,意识状态改变、糖尿病、心房颤动、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年龄、脉率、血清白蛋白、舒张压、pH值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30天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SI评分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的30天内全因死亡及不良结局预测效能最佳,DECAF评分最差。但PSI评分操作比较繁琐,因此,有待开发并验证针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的专属预后评估工具,以更好指导治疗策略的选择。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2019年的中国疾病负担结果显示,慢阻肺已居我国居民死亡病因的第3位 [1]。慢阻肺急性加重是慢阻肺患者住院和死亡的重要原因,住院死亡率可达7.52%[2]。社区获得性肺炎(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是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患者的常见合并症,研究提示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较单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不良结局明显增多,包括机械通气、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入住、住院时间延长、急性加重再入院及院内死亡等[3–8],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的住院患者进行早期准确的预后评估有利于指导治疗策略的选择及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并希望通过对高危患者的及时干预改善其预后。
目前,针对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和CAP患者均有一些预后预测模型,比如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常用的预后模型有BAP-65评分和DECAF评分,CAP患者常用的预后模型有CURB-65评分和肺炎严重程度评分(pneumonia severity index,PSI)。以上4种评分均在内部及外部验证队列中显示出良好的性能[9]。但是鉴于临床实践中,慢阻肺急性加重和CAP常合并存在,目前尚缺乏经过验证的适合这一人群的预后评估模型。本研究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的回顾性研究,评估和比较了BAP-65、CURB-65、DECAF和PSI 4种临床预后评分在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住院患者30天内死亡和不良结局方面的效能,并同时探讨了这类患者短期死亡的危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对象来源于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牵头的一项全国、多中心的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患者的注册登记研究(简称MAGNET研究)。该注册登记研究前瞻性连续纳入了国内10 家大型综合三甲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乐山市人民医院、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2017年9月—2021年7月因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治疗的患者,收集患者入院时的基本情况、症状及体征、相关实验室检查及影像结果、治疗措施及预后等临床资料,并随访患者的预后。本研究从上述注册登记研究纳入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中筛选出合并CAP诊断的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慢阻肺急性加重和CAP的诊断经过两位经验丰富的临床专家复核。参照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2021年修订版)》作为慢阻肺急性加重的诊断标准。CAP的诊断标准参照《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指南(2016版)》。研究对象入选标准为:① 因慢阻肺急性加重就诊的住院患者;② 同时符合CAP诊断标准;③ 年龄>40岁。排除标准:① 住院时间<48 h;② 缺乏入院后30天随访资料或临床资料不完整。本研究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医学伦理分委会批准(2019年审1056号),并获得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编号:ChiCTR2100044625。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收集患者入院时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吸烟史等;合并症,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支气管扩张、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恶性肿瘤等;入院时的症状及体征,包括胸痛、呼吸困难、意识障碍、脉率、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呼吸频率等;相关实验室指标及影像结果(入院后首次结果),包括血红蛋白、白细胞计数、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心肌标志物、尿素氮、血气分析及胸部CT结果等;不良预后,包括30天内接受有创机械通气、入住ICU和全因死亡。
1.2.2 分组
将患者按照入院起至第30天是否死亡分为死亡组和生存组进行病例对照研究。比较两组患者入院时基础情况、合并症、相关辅助检查及预后等指标的差异。
1.2.3 预后预测模型评分
基于纳入的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入院时的临床资料,分别采用BAP-65、DECAF、CURB-65和PSI评分4种量表回顾性对患者进行评分及危险分级。 4种评分量表纳入的因素和评分标准如下。
(1)BAP-65评分包括血尿素氮≥7 mmol/L、意识状态改变、脉率≥109 次/min和年龄>65岁以上4个危险因素,根据年龄及风险因素分为Ⅰ~Ⅴ级,为便于模型间的比较,将Ⅰ~Ⅴ级分别赋予1~5分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
(2)DECAF评分包括呼吸困难程度、嗜酸性粒细胞减少(<0.05×109/L)、酸中毒(pH<7.3)、合并肺实变和心房颤动5个危险因素,DECAF评分中的呼吸困难程度采用扩展的英国医学委员会呼吸困难量表进行评价。呼吸困难根据程度赋予1分或2分,其余4项各为1分,其中,低风险为0~1分,中风险为2分,高风险为≥3分。
(3)CURB-65评分包括年龄≥65岁、意识错乱、收缩压<90 mm Hg(1 mm Hg=0.133 kPa)或舒张压<60 mm Hg、呼吸频率≥30次/min和血尿素氮>7 mmol/L共5个因素,每一个因素为1分,其中,低风险为0~1分,中风险为2分,高风险为≥3分。
(4)PSI评分有20个变量,包括人口学因素{年龄[男性,多少岁即多少分;女性,计为(年龄–10)分],护理院居住(10分)}、基础疾病[肿瘤(30分)、肝病(20分)、充血性心力衰竭(10分)、肾脏病(10分)、脑血管疾病(10分)]、异常体格检查[神志改变(20分)、呼吸≥30次/min(20分)、收缩压<90 mm Hg(20分)、体温<35 ℃或≥40 ℃(15分)、脉率≥125次/min(10分)]和辅助检查结果[pH<7.35(30分)、血尿素氮≥30 mg/dL(20分)、血清钠<130 mmol/L(20分)、血糖≥250 mg/dL(10分)、PaO2<60 mm Hg(10分)、血细胞比容<30%(10分)、胸腔积液(10分)]。根据得出的分数,分为Ⅰ~Ⅴ级,其中,Ⅰ、Ⅱ级为评分≤70分,但Ⅰ级的年龄<50岁且无基础疾病,Ⅲ级为71~90分,Ⅳ级为91~130分,Ⅴ级为>130分。
1.2.4 研究结局
主要研究结局是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的全因死亡。次要研究结局是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 30天内相关的总体不良结局,包括全因死亡、有创机械通气或入住ICU,发生上述三个不良结局中的任意一个及以上即定义为不良预后。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8.0统计软件。使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使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Q1,Q3)]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以例(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基于单因素分析结果,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死亡的可能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寻30天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值及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采用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来评估和比较四种量表预测短期死亡及总体不良结局的准确性,并分别计算4个量表的敏感性及特异性。采用Z检验两两比较4种量表的AUC。统计学检验为双尾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使用中位数(四分位数)[M(Q1,Q3)]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以例(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基于单因素分析结果,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死亡的可能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以探寻30天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OR)值及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采用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AUC)来评估和比较四种量表预测短期死亡及总体不良结局的准确性,并分别计算4个量表的敏感性及特异性。采用Z检验两两比较4种量表的AUC。统计学检验为双尾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MAGNET研究共纳入了14007例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患者,其中3375例患者合并CAP诊断并符合纳入标准。纳入患者中男2545例,女830例,平均年龄(73.66±10.73)岁。入院30天内,129例患者发生死亡,614例患者发生不良结局,全因死亡率为3.82%,不良结局率为18.19%。
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死亡组患者的年龄为(81.39±8.94)岁,明显高于生存组[(73.35±10.68)岁,P<0.001]。在性别、体重指数、吸烟史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死亡组有意识状态改变的患者比例为41.1%,明显高于生存组(5.9%,P<0.001)。两组在呼吸困难、心悸、胸痛的发生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死亡组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房颤动、心力衰竭、慢性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生存组(均P<0.05)。两组在合并恶性肿瘤、肺栓塞、肝脏疾病的人数比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死亡组患者的脉率为(95.12±20.55)次/min,明显高于生存组的(89.85±16.60)次/min(P<0.05);死亡组患者的平均舒张压和动脉压分别为(68.43±16.02)mm Hg和(88.29±16.84)mm Hg,明显低于生存组[分别为(77.25±12.97)mm Hg和(95.19±13.50)mm Hg](均P<0.001)。两组患者在体温、呼吸频率、收缩压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死亡组患者的氧分压、白细胞计数、肌酐、尿素氮、合并胸腔积液的比例,明显高于生存组(均P<0.05)。死亡组患者的pH值、血红蛋白、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白蛋白水平均明显低于生存组(均P<0.05)。两组患者在二氧化碳分压、血清钠、肺大疱的比例及CT显示右心室扩张的比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死亡组的中位住院时间为17 d,明显长于生存组(11 d,P<0.001);接受有创机械通气率和ICU入住率分别为43.3%和42.6%,均明显高于生存组(7.3%,P<0.001;13.2%,P<0.001)。结果见表1。
 )/例(%)]
)/例(%)]
2.2 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中发现可能与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全因死亡相关的因素有:年龄、意识状态改变,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心房颤动、心力衰竭、慢性肾病,脉率、舒张压、平均动脉压、pH值、氧分压、血红蛋白、白细胞计数、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血尿素氮、肌酐、白蛋白,合并胸腔积液,将以上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意识状态改变(OR=4.809,95%CI 2.931~7.889,P<0.001)、糖尿病(OR=2.052,95%CI 1.229~3.426,P=0.006)、心房颤动(OR=1.829,95%CI 1.020~3.281,P=0.043)、慢性肺源性心脏病(OR=1.644,95%CI 1.032~2.619,P=0.036 )、年龄(OR=1.075,95%CI 1.045~1.106,P<0.001)、脉率(OR=1.018,95%CI 1.005~1.031,P=0.006)、血清白蛋白(OR=0.946,95%CI 0.906~0.988,P=0.013)、舒张压(OR=0.942,95%CI 0.900~0.986,P=0.010)、pH值(OR=0.031,95%CI 0.001~0.656,P=0.026)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30天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见表2。
2.3 4种预后模型的预测效能比较
使用4种预后量表对纳入的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进行评分及死亡风险分级,结果见表3。ROC 曲线结果显示CURB-65评分、BAP-65评分、DECAF评分、PSI评分在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不良预后方面均有一定价值,预测全因死亡的AUC分别是0.780(95%CI 0.737~0.823)、0.782(95%CI 0.741~0.824)、0.614(95%CI 0.566~0.663)、0.816(95%CI 0.780~0.853),均P<0.001;预测总体不良结局的AUC分别是0.694(95%CI 0.669~0.719)、0.687(95%CI 0.663~0.712)、0.564(95%CI 0.539~0.590)、0.705(95%CI 0.682~0.728),均P<0.001(图1、图2及表4)。PSI评分对全因死亡及总体不良结局预测效能均最佳,DECAF评分最差。分别两两进行Z检验,结果提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图1
4种量表预测30天内全因死亡的ROC 曲线
图1
4种量表预测30天内全因死亡的ROC 曲线
 图2
4种量表预测30天内不良结局的ROC曲线
图2
4种量表预测30天内不良结局的ROC曲线
3 讨论
国外文献报道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住院死亡率约为11%[5],本项在中国人群的研究发现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死亡率为3.82%,低于国外人群研究结果。另一项纳入1215例患者的中国研究显示,慢阻肺合并CAP的住院死亡率2.7%[10],与我们的研究结果接近。国内外研究一致的发现是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短期死亡率明显高于单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5,10],比如MAGNET研究中单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死亡率为1.4%,而上述提到的另一项中国患者中进行的研究发现单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住院死亡率为0.9%[10]。这提示合并CAP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预后更差,临床实践中应尤其关注这类患者,早期准确评估其预后以指导治疗策略的选择。
意识状态改变、合并糖尿病、合并心房颤动、合并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老龄、脉率增快、血清白蛋白降低、舒张压降低、pH值降低在本研究中被证实为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的短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些研究发现基本与既往在慢阻肺急性加重或CAP患者中的文献报道一致[11–13]。另有研究认为心血管疾病[14]、嗜酸性粒细胞[15]、C反应蛋白[6]、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评分[6]是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死亡预测指标,即低舒张压,而收缩压与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的全因死亡无关。舒张压是临床容易测量的指标,既往研究证实低舒张压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及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死亡风险[16–18],潜在的机制可能有如下两点:一是因为冠状动脉的血流供应主要来自于舒张期,心肌灌注严重依赖于舒张压,较低的舒张压可能导致心肌低灌注和相关的心肌损伤[19];二是大动脉弹性下降时,其大动脉的弹性储器作用减弱而降低舒张压,提示这些舒张压低的患者大动脉的僵硬程度更高,一般健康情况更差18。但是低舒张压增加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死亡风险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是否也是通过上述机制起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
BAP-65和DECAF评分是用于评估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预后的评估模型,CURB-65和PSI评分是用于评估CAP患者预后的评估模型。对于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人群,哪种预后评估模型更优尚没有一致的结论,且相关的研究也很少。我们的研究是第一个在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的住院患者中验证和比较BAP-65、DECAF、CURB-65和PSI评分准确性的大样本多中心研究。研究发现PSI评分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全因死亡及总体不良结局的效能最佳,而DECAF评分最差。PSI评分最开始被开发用于评价肺炎的严重程度,通过人口学因素、基础疾病、异常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结果等20个参数进行预后评价。有研究表明,PSI评分也可用于预测住院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住院死亡风险,且预后能力优于CURB-65和BAP-65评分[20],这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的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全因死亡的可能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意识状态改变、脑血管疾病、心力衰竭、慢性肾病、脉率、pH值、氧分压、血尿素氮、胸腔积液,均包含在PSI评分的参数当中,其中年龄、意识状态改变、脉率、pH值是独立的危险因素。但PSI评分较其他评分相比较繁琐,操作复杂,且有些参数临床不易获取,如轻症患者可能不会进行血气分析检测等,一定程度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应用。既往的研究发现DECAF评分在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住院患者院内及早期死亡和对于低风险人群认定的准确性方面展示出良好的效能[21]。DECAF评分包括呼吸困难(D)、嗜酸性粒细胞减少(E)、肺实变(C)、酸中毒(A)和心房颤动(F)这 5 个易于临床获取的变量。但是在我们的研究人群中其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早期死亡及总体不良结局的准确性较差。既往研究发现该评分虽然对低风险人群的认定有很好的准确性,但对于高风险人群的划分准确性较差,阳性似然比仅1.80[21]。预测效能较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该量表中呼吸困难的评估是基于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稳定期的状态,具有一定主观性,同时这种回忆性的评分也容易造成评分的不准确。
CURB-65及BAP-65评分分别用于CAP及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预后评估,二者纳入的指标很相似:CURB-65评分共5项指标,包括意识障碍,呼吸频率,收缩压或舒张压,年龄和血尿素氮,《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6年版)》[22]建议使用CURB-65评分作为判断CAP患者是否需要住院治疗的标准。BAP-65评分共4项指标,包括意识状态改变、脉率、年龄及血尿素氮,是由Tabak等[23]于2009年开发用于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使用机械通气的可能性及死亡风险的预后量表。这两种评分简单易操作,广泛应用于临床中,但是它们主要以年龄及生命体征作为评价标准,未结合更多的辅助检查项目,导致预测效能有一定局限性。不少研究显示,CURB-65评分及BAP-65评分对于慢阻肺急性加重和(或)CAP院内死亡[20-21, 24-25]或30天死亡[21]的预测效能较差,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的患者预后差,不良结局多。目前国内外有关上述4种评分对于包括有创机械通气、入住ICU、全因死亡在内的整体不良结局预测价值比较的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结果尚存在争议。有研究显示,BAP-65比CURB-65更准确地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需要机械通气的风险,AUC分别为0.78比0.74[26];也有研究表明BAP-65预测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需要有创机械通气的能力较差,AUC仅0.61[25]。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PSI、CURB-65及BAP-65评分对于不良结局都有不错的预测效果,其中PSI评分最佳;但DECAF评分预测效果较差。
综上,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30天内死亡率及不良结局发生率较高,意识状态改变、糖尿病、心房颤动、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年龄、脉率、血清白蛋白、舒张压、pH值是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30天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SI评分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的30天内全因死亡及不良结局预测效能最佳,DECAF评分最差。但PSI评分操作比较繁琐,因此,有待开发并验证针对慢阻肺急性加重合并CAP患者的专属预后评估工具,以更好指导治疗策略的选择。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