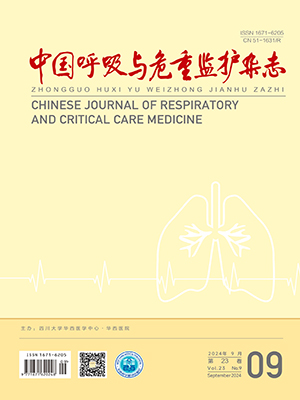引用本文: 陈雨莎, 袁梦鑫, 梁斌苗, 欧雪梅. 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并细胞免疫功能缺陷致支气管扩张、肝硬化一例并文献复习.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19, 18(2): 169-173. doi: 10.7507/1671-6205.201805046 复制
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common variable immune deficiency,CVID)是一种以严重低免疫球蛋白血症和反复感染为临床特点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在北美和欧洲是引起儿童和成人抗体缺陷的最常见病因,但在我国发病率较低,属于罕见病[1]。其病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可能与 B 细胞功能异常以及 T 细胞及抗原提呈细胞缺失有关[2-3]。临床表现为反复的呼吸系统及消化系统感染,常伴发慢性肺部疾病、肉芽肿、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脾脏增大,甚至伴发淋巴增殖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4]。其主要特点是免疫球蛋白水平降低和反复感染,其中以呼吸道感染最为常见[5]。现报告我院近期诊断的 1 例 CVID 并细胞免疫功能缺陷致支气管扩张、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复习 CVID 的临床特点、诊断方法及治疗手段,以提高临床医师对此病认识,减少误漏诊。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52 岁,因“反复咳嗽、咳痰 20+年,间断双下肢水肿 7 年,加重 3 个月”于 2018 年 1 月 5 日收入院。20+年前患者开始于受凉后出现咳嗽、咯黄色黏痰,在当地医院给予静脉滴注“抗生素”治疗(具体不详)后症状可好转。2015 年开始上述病情发作逐渐频繁,主要表现为咳嗽、咯黄痰和活动后呼吸困难,开始不能从事日常体力劳动,期间多次住院治疗,均诊断为“肺部感染”。7 年前,患者开始出现间断双下肢水肿,夜间喜高枕卧位。上述症状频繁发作,平均每月 2~3 次,每次均需静脉使用抗生素后症状方缓解。患者日常活动严重受限,近 1 年几乎无法外出活动。3 个月前,患者上述症状再次加重,且反复发热,体温波动在 38~39 ℃ 之间,来我院就诊收入住院治疗。患者长期生活在甘肃地区,居住地平均海拔 2 700 m。否认吸烟史、生物燃料接触史、幼年反复呼吸道感染病史。否认家族或近亲中有类似病史。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慢性病容,皮肤巩膜无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未扪及肿大。颈静脉怒张。心界稍向左扩大,心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杂音。胸廓未见异常,双肺闻及大量干湿啰音。腹部外形正常,全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肋下 2 横指,脾肾未触及。双下肢轻度水肿。辅助检查:血常规:血红蛋白 181 g/L,白细胞 7.29×109/L,中性分叶核粒细胞百分率 78.7%。降钙素原 0.15 ng/ml。痰培养:卡他莫拉菌生长。生化:总蛋白 51.1 g/L,球蛋白 15.0 g/L,BNP 652 pg/ml。体液免疫:IgG<0.33 g/L(参考值 8~15.5 g/L),IgA<66.70 mg/L(参考值 836~2 900 mg/L),IgM 5 740 mg/L(参考值 700~2 200 mg/L)。各项肝炎抗体、类风湿因子、自免肝抗体及所有自身免疫相关抗体检测均阴性。B 细胞绝对计数:155 个/µl(175~322)。T 细胞绝对计数:CD4+T 246 个/µl,CD4/CD8 0.27。全血流式细胞检测未见异常表型细胞群。EB 病毒、巨细胞病毒、结核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血清蛋白电泳、免疫固定电泳无异常均无明显异常。血凝集素、Coomb 试验(–)。胸部 CT:双肺散在结节、斑片影,双肺部分支气管稍扩张,管壁增厚,部分支气管内少许黏液栓形成;双肺不均匀气肿;双肺门区软组织影增多,肿大淋巴结?心脏增大,右心房为著;纵隔淋巴结长大;肺动脉主干及左右肺动脉干增粗;右侧胸腔少量积液(图 1)。头部 CT:副鼻窦炎。腹部 CT:肝硬化,脾大,门脉高压,轻度侧枝循环开放,腹腔内淋巴结增多,部分增大。心脏彩超:右心稍大;肺动脉增宽,肺动脉高压,双室收缩功能测值正常。肺功能: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和用力肺活量的比值 52.28%,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 34.4%,残气量/肺总量的比值 182.4%,肺一氧化碳弥散量 38.1 ml/(min·mm Hg)。纤维支气管镜:管腔未见明显异常;肺泡灌洗液未查见恶性细胞。腹部彩超:肝脏数个实性结节,脾脏长大。肝脏超声造影:左肝实性结节,考虑多为增生结节。胃镜:食管静脉曲张(中度)。骨髓穿刺涂片+活检:增生活跃,成熟红细胞呈厚层分布;流式细胞检测未见明显异常表型细胞群。结合患者反复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的病史,以及免疫相关检查结果,拟诊为 CVID 并细胞免疫缺陷、支气管扩张、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肝硬化、门脉高压。给予抗感染、解痉、祛痰、利尿等治疗,并输注丙种球蛋白 20 g。患者症状好转出院。1 个月后随访患者咳嗽咳痰及呼吸困难症状明显改善,日常活动耐量明显提高。嘱患者院外定期输注丙种球蛋白和胸腺肽治疗。来我院常规随访 2 次,自诉在当地医院注射过 3 次免疫球蛋白,反馈效果不错,现在可以自由外出活动。
 图1
胸部 CT 检查像
图1
胸部 CT 检查像
a. 肺窗,可见双肺感染灶及支气管扩张(白箭);b. 纵隔窗,可见肺动脉明显增宽
2 文献复习
以“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或“普通变异型免疫缺陷病”或“寻常变异性免疫缺陷病”或“寻常变异型免疫缺陷病”“低免疫球蛋白血症”为关键词检索万方数据库和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以“common variable immunodeficiency”为关键词检索 PubMed、Ovid、Embase 及 Cochrane 数据库,检索时间为 1970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共检索到 288 篇文献包括 8 000 余例 CVID 患者,除国外一篇对 2 212 个病例的汇总分析以外[6],大部分为散发报道或仅有数十个病例的集中报道。现结合这些文献进行分析总结。
2.1 概述
CVID 是一种特异性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主要表现是全身多系统的反复感染,以呼吸系统最为常见,并有淋巴结、脾肿大,容易并发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恶性肿瘤[7]。据文献报道,国外发病率大约在 1:50 000~1:25 000 之间[6],是北美和欧洲引起儿童和成人抗体缺陷的最常见病因。而在国内发病情况则相对罕见。
2.2 发病机制
有关发病机制的研究观点现大多倾向于 B 细胞缺乏导致抗体产生减少。其中外周 B 细胞数量的减少、终末 B 细胞分化为记忆 B 细胞和浆细胞的过程受损以及 CD27+ B 细胞子集的增多是主要的发病环节[8]。在基因机制的研究上,目前文献报道了 TNFRSF13B 突变、C104R 基因序列突变、TLR7 和 TLR9 突变[9-10]与此病有一定联系。
2.3 发病时间及诊断时间
在 10 岁以前出现首发症状的患者占到了 33.7%。在这部分人群中,男童的比例(39.8%)高于女童(27.9%)。两个诊断高峰期分别为童年时期及 30~40 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症状的不特异性,平均诊断延迟时间长达 4.1 年(诊断每延迟 1 年,患者死亡风险增加 4.5%)。
2.4 临床表现
CVID 的临床表现存在高度异质性。对 2 212 例的大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本病的临床表现包括肺炎(32%)、自身免疫性疾病(29%)、脾大(26%)、支气管扩张(23%)、肉芽肿性炎(9%)、肠病(9%)、实体肿瘤(5%)、脑炎或脑膜炎(4%)、淋巴瘤(3%)[6]。其中反复感染是最主要和最常见的症状[6]。感染部位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呼吸系统、胃肠道、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皮肤以及肝脏的感染[8]。CVID 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以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最为常见,其他还包括皮肌炎、类风湿关节炎[11]。除常见的支气管扩张外,CVID 合并的肺部病变还包括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等[12-13]。此外,10% CVID 患者合并有肝脏损害[14],包括碱性磷酸酶升高、结节性再生性增生、肝硬化及其并发症,其机制可能与自身免疫相关。
2.5 辅助检查
CVID 的实验室检查多表现为血清中免疫球蛋白总量减少。其中 IgG、IgA 常缺如或减少,而 IgM 有时可增多。合并细胞免疫功能缺陷者 CD4 细胞绝对计数常降低。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者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Coombs 试验常为阳性。其影像学检查多无特征性,常可表现为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纤维化、肝硬化及脾大等征象。彩超还可发现全身多处淋巴结长大。
2.6 诊断标准
CVID 诊断目前参考 2014 年欧洲免疫缺陷协会和全美免疫缺陷组所发布的指南[15]。主要包括四项内容。A(需满足全部以下 3 点):① 成人 IgG<5 g/L;② 没有其他确定原因的免疫缺陷;③ 年龄大于 4 岁。B:存在免疫系统缺陷的临床证据,符合以下 1 项及更多项:① 反复、严重的和不寻常的感染;② 使用抗菌药物效果差;③ 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仍出现严重感染;④ 已接种疫苗或有免疫的病原体仍出现感染;⑤ 炎症性疾病支气管扩张和(或)慢性鼻窦炎;⑥ 炎症性疾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肉芽肿性炎等)。C:符合以下 3 条及更多项:① IgA<0.8 g/L 和(或)IgM<0.4 g/L;② B 细胞存在但记忆 B 细胞子集减少和(或)CD21 子集增多;③ IgG3<0.2 g/L;④ 疫苗不良反应相对于同龄人难以控制;⑤ 疫苗效果相对于同龄人短暂;⑥ 血球凝集素缺乏(非 AB 血型);⑦ 血清学支持自身免疫性疾病;⑧ 基因序列突变如 TACI 等一系列实验室检查,对于诊断没有特异性,但是如果阳性则有助于诊断。D:相关组织学证据:① 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② 肉芽肿性疾病;③ 肝脏结节性增生;④ 胃肠道结节性淋巴样组织增生;⑤ 胃肠道组织活检未见浆细胞。上述四项内容中,满足 ABC 或 ABD 可拟诊为 CVID,若只满足 A、AC、AB、AD 则仅能疑诊 CVID。
2.7 治疗及预后
目前对 CVID 的治疗主要为免疫球蛋白替代疗法。来自不同中心的病例对照研究分析发现,给予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平均剂量为 460 mg/kg,注射间隔时间为 30 d,可以使患者肺炎发生率明显降低;少数患者因治疗开始时间较晚且合并了严重的支气管扩张或淋巴瘤而最终死亡。因此指南建议免疫球蛋白替代疗法的起始量为 0.4~0.6 g/kg,每个月 1 次静脉滴注[16],合并支气管扩张者主张给予较高剂量的的免疫球蛋白治疗[6]。预防性使用抗体和保护性隔离对 CVID 患者有益处[17]。如患者合并细胞免疫功能缺陷,需注意禁用活疫苗。
如能早期诊断并适当治疗,患者预后较好[6]。死因多为难以控制的肺部感染或并发淋巴瘤或实体瘤。
3 讨论
本例患者既往多年“肺部感染”病史,多次胸部 CT 均提示支气管扩张,且反复使用抗生素效果不佳,后期逐渐发展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结合患者相关检查,符合诊断标准中的 ABC 及部分 D 条目,达到拟诊 CVID 标准。因此,考虑本例患者为 CVID 合并细胞免疫缺陷导致支气管扩张、肝硬化、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但仔细阅读患者胸部 CT 可发现,患者双肺仅部分支气管扩张、管壁增厚,其病变范围和程度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严重程度不完全一致。且肺功能提示该患者除重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外,同时存在严重弥散功能降低,无法完全用支气管扩张解释。分析其原因可能为:第一,由于患者存在支气管扩张、管壁增厚,用力肺活量降低,导致 V/Q 比例失调;第二,该例属少见的肝脏受累患者,既往研究表明肝硬化的存在可以使肝脏对循环中肺血管舒张因子的清除功能以及对门静脉中多种血管活性因子的代谢功能丧失[18],由此可致肺内血管扩张,V/Q 比例失调。这两方面原因可解释患者严重低氧血症、肺动脉高压及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因此,本例患者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原因除了反复感染所致的支气管扩张外,还与 CVID 肝脏受累导致肺通气血流比失调有关。
此外,本例患者还同时合并有外周血 CD4+T 细胞绝对计数、CD4/CD8 比例下降,骨髓流式细胞学提示 CD4+T 细胞占比下降。提示该患者同时存在细胞免疫功能缺陷。Takahashi 等[19]和 Malphettes 等[20]报道部分 CVID 患者可以同时合并细胞免疫功能缺陷,其机制可能与 T 细胞对分裂素和抗原刺激的反应下降及凋亡增加相关[21]。这也是本例患者频繁发生肺部感染的原因之一。
在本例患者在长达 20 余年的病程中,反复诊断为肺部感染并给予抗感染治疗。但病情仍频繁发生,近 1 年患者几乎每个月均需无间断地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在既往整个诊治过程,从未对其反复发生肺部感染的原因进行筛查。此次诊断明确后给予免疫球蛋白治疗,患者出院后 1 个月未再发生肺部感染及使用抗生素。因此明确诊断并及时治疗是控制本病的关键。基于这一疾病缺乏特异性症状、难发现、易误漏诊的特点,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基金会提出了 CVID 的预警症状包括:一年中有 8 次或 8 次以上的中耳炎,2 次或 2 次以上的严重鼻窦炎、肺炎、非常见部位感染,反复发生的深部皮肤或脏器感染,非常见或条件性致病菌感染以及家族中有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病史者[22]。因此,临床中对于反复发生的感染且治疗效果较差时需高度警惕该病的可能并注意鉴别诊断,避免漏诊或仅诊断为免疫功能低下而停止进一步病因的深究,以致患者不能得到及时诊断及治疗。
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common variable immune deficiency,CVID)是一种以严重低免疫球蛋白血症和反复感染为临床特点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在北美和欧洲是引起儿童和成人抗体缺陷的最常见病因,但在我国发病率较低,属于罕见病[1]。其病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可能与 B 细胞功能异常以及 T 细胞及抗原提呈细胞缺失有关[2-3]。临床表现为反复的呼吸系统及消化系统感染,常伴发慢性肺部疾病、肉芽肿、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脾脏增大,甚至伴发淋巴增殖性疾病及恶性肿瘤等[4]。其主要特点是免疫球蛋白水平降低和反复感染,其中以呼吸道感染最为常见[5]。现报告我院近期诊断的 1 例 CVID 并细胞免疫功能缺陷致支气管扩张、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复习 CVID 的临床特点、诊断方法及治疗手段,以提高临床医师对此病认识,减少误漏诊。
1 临床资料
患者女性,52 岁,因“反复咳嗽、咳痰 20+年,间断双下肢水肿 7 年,加重 3 个月”于 2018 年 1 月 5 日收入院。20+年前患者开始于受凉后出现咳嗽、咯黄色黏痰,在当地医院给予静脉滴注“抗生素”治疗(具体不详)后症状可好转。2015 年开始上述病情发作逐渐频繁,主要表现为咳嗽、咯黄痰和活动后呼吸困难,开始不能从事日常体力劳动,期间多次住院治疗,均诊断为“肺部感染”。7 年前,患者开始出现间断双下肢水肿,夜间喜高枕卧位。上述症状频繁发作,平均每月 2~3 次,每次均需静脉使用抗生素后症状方缓解。患者日常活动严重受限,近 1 年几乎无法外出活动。3 个月前,患者上述症状再次加重,且反复发热,体温波动在 38~39 ℃ 之间,来我院就诊收入住院治疗。患者长期生活在甘肃地区,居住地平均海拔 2 700 m。否认吸烟史、生物燃料接触史、幼年反复呼吸道感染病史。否认家族或近亲中有类似病史。入院查体:生命体征平稳。慢性病容,皮肤巩膜无黄染,全身浅表淋巴结未扪及肿大。颈静脉怒张。心界稍向左扩大,心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杂音。胸廓未见异常,双肺闻及大量干湿啰音。腹部外形正常,全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肋下 2 横指,脾肾未触及。双下肢轻度水肿。辅助检查:血常规:血红蛋白 181 g/L,白细胞 7.29×109/L,中性分叶核粒细胞百分率 78.7%。降钙素原 0.15 ng/ml。痰培养:卡他莫拉菌生长。生化:总蛋白 51.1 g/L,球蛋白 15.0 g/L,BNP 652 pg/ml。体液免疫:IgG<0.33 g/L(参考值 8~15.5 g/L),IgA<66.70 mg/L(参考值 836~2 900 mg/L),IgM 5 740 mg/L(参考值 700~2 200 mg/L)。各项肝炎抗体、类风湿因子、自免肝抗体及所有自身免疫相关抗体检测均阴性。B 细胞绝对计数:155 个/µl(175~322)。T 细胞绝对计数:CD4+T 246 个/µl,CD4/CD8 0.27。全血流式细胞检测未见异常表型细胞群。EB 病毒、巨细胞病毒、结核 γ 干扰素释放试验、血清蛋白电泳、免疫固定电泳无异常均无明显异常。血凝集素、Coomb 试验(–)。胸部 CT:双肺散在结节、斑片影,双肺部分支气管稍扩张,管壁增厚,部分支气管内少许黏液栓形成;双肺不均匀气肿;双肺门区软组织影增多,肿大淋巴结?心脏增大,右心房为著;纵隔淋巴结长大;肺动脉主干及左右肺动脉干增粗;右侧胸腔少量积液(图 1)。头部 CT:副鼻窦炎。腹部 CT:肝硬化,脾大,门脉高压,轻度侧枝循环开放,腹腔内淋巴结增多,部分增大。心脏彩超:右心稍大;肺动脉增宽,肺动脉高压,双室收缩功能测值正常。肺功能: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和用力肺活量的比值 52.28%,FEV1占预计值百分比 34.4%,残气量/肺总量的比值 182.4%,肺一氧化碳弥散量 38.1 ml/(min·mm Hg)。纤维支气管镜:管腔未见明显异常;肺泡灌洗液未查见恶性细胞。腹部彩超:肝脏数个实性结节,脾脏长大。肝脏超声造影:左肝实性结节,考虑多为增生结节。胃镜:食管静脉曲张(中度)。骨髓穿刺涂片+活检:增生活跃,成熟红细胞呈厚层分布;流式细胞检测未见明显异常表型细胞群。结合患者反复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的病史,以及免疫相关检查结果,拟诊为 CVID 并细胞免疫缺陷、支气管扩张、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肝硬化、门脉高压。给予抗感染、解痉、祛痰、利尿等治疗,并输注丙种球蛋白 20 g。患者症状好转出院。1 个月后随访患者咳嗽咳痰及呼吸困难症状明显改善,日常活动耐量明显提高。嘱患者院外定期输注丙种球蛋白和胸腺肽治疗。来我院常规随访 2 次,自诉在当地医院注射过 3 次免疫球蛋白,反馈效果不错,现在可以自由外出活动。
 图1
胸部 CT 检查像
图1
胸部 CT 检查像
a. 肺窗,可见双肺感染灶及支气管扩张(白箭);b. 纵隔窗,可见肺动脉明显增宽
2 文献复习
以“普通变异性免疫缺陷病”或“普通变异型免疫缺陷病”或“寻常变异性免疫缺陷病”或“寻常变异型免疫缺陷病”“低免疫球蛋白血症”为关键词检索万方数据库和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以“common variable immunodeficiency”为关键词检索 PubMed、Ovid、Embase 及 Cochrane 数据库,检索时间为 1970 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共检索到 288 篇文献包括 8 000 余例 CVID 患者,除国外一篇对 2 212 个病例的汇总分析以外[6],大部分为散发报道或仅有数十个病例的集中报道。现结合这些文献进行分析总结。
2.1 概述
CVID 是一种特异性的原发性免疫缺陷病。主要表现是全身多系统的反复感染,以呼吸系统最为常见,并有淋巴结、脾肿大,容易并发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恶性肿瘤[7]。据文献报道,国外发病率大约在 1:50 000~1:25 000 之间[6],是北美和欧洲引起儿童和成人抗体缺陷的最常见病因。而在国内发病情况则相对罕见。
2.2 发病机制
有关发病机制的研究观点现大多倾向于 B 细胞缺乏导致抗体产生减少。其中外周 B 细胞数量的减少、终末 B 细胞分化为记忆 B 细胞和浆细胞的过程受损以及 CD27+ B 细胞子集的增多是主要的发病环节[8]。在基因机制的研究上,目前文献报道了 TNFRSF13B 突变、C104R 基因序列突变、TLR7 和 TLR9 突变[9-10]与此病有一定联系。
2.3 发病时间及诊断时间
在 10 岁以前出现首发症状的患者占到了 33.7%。在这部分人群中,男童的比例(39.8%)高于女童(27.9%)。两个诊断高峰期分别为童年时期及 30~40 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症状的不特异性,平均诊断延迟时间长达 4.1 年(诊断每延迟 1 年,患者死亡风险增加 4.5%)。
2.4 临床表现
CVID 的临床表现存在高度异质性。对 2 212 例的大样本数据分析发现,本病的临床表现包括肺炎(32%)、自身免疫性疾病(29%)、脾大(26%)、支气管扩张(23%)、肉芽肿性炎(9%)、肠病(9%)、实体肿瘤(5%)、脑炎或脑膜炎(4%)、淋巴瘤(3%)[6]。其中反复感染是最主要和最常见的症状[6]。感染部位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呼吸系统、胃肠道、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皮肤以及肝脏的感染[8]。CVID 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以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最为常见,其他还包括皮肌炎、类风湿关节炎[11]。除常见的支气管扩张外,CVID 合并的肺部病变还包括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等[12-13]。此外,10% CVID 患者合并有肝脏损害[14],包括碱性磷酸酶升高、结节性再生性增生、肝硬化及其并发症,其机制可能与自身免疫相关。
2.5 辅助检查
CVID 的实验室检查多表现为血清中免疫球蛋白总量减少。其中 IgG、IgA 常缺如或减少,而 IgM 有时可增多。合并细胞免疫功能缺陷者 CD4 细胞绝对计数常降低。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者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Coombs 试验常为阳性。其影像学检查多无特征性,常可表现为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纤维化、肝硬化及脾大等征象。彩超还可发现全身多处淋巴结长大。
2.6 诊断标准
CVID 诊断目前参考 2014 年欧洲免疫缺陷协会和全美免疫缺陷组所发布的指南[15]。主要包括四项内容。A(需满足全部以下 3 点):① 成人 IgG<5 g/L;② 没有其他确定原因的免疫缺陷;③ 年龄大于 4 岁。B:存在免疫系统缺陷的临床证据,符合以下 1 项及更多项:① 反复、严重的和不寻常的感染;② 使用抗菌药物效果差;③ 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仍出现严重感染;④ 已接种疫苗或有免疫的病原体仍出现感染;⑤ 炎症性疾病支气管扩张和(或)慢性鼻窦炎;⑥ 炎症性疾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肉芽肿性炎等)。C:符合以下 3 条及更多项:① IgA<0.8 g/L 和(或)IgM<0.4 g/L;② B 细胞存在但记忆 B 细胞子集减少和(或)CD21 子集增多;③ IgG3<0.2 g/L;④ 疫苗不良反应相对于同龄人难以控制;⑤ 疫苗效果相对于同龄人短暂;⑥ 血球凝集素缺乏(非 AB 血型);⑦ 血清学支持自身免疫性疾病;⑧ 基因序列突变如 TACI 等一系列实验室检查,对于诊断没有特异性,但是如果阳性则有助于诊断。D:相关组织学证据:① 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② 肉芽肿性疾病;③ 肝脏结节性增生;④ 胃肠道结节性淋巴样组织增生;⑤ 胃肠道组织活检未见浆细胞。上述四项内容中,满足 ABC 或 ABD 可拟诊为 CVID,若只满足 A、AC、AB、AD 则仅能疑诊 CVID。
2.7 治疗及预后
目前对 CVID 的治疗主要为免疫球蛋白替代疗法。来自不同中心的病例对照研究分析发现,给予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平均剂量为 460 mg/kg,注射间隔时间为 30 d,可以使患者肺炎发生率明显降低;少数患者因治疗开始时间较晚且合并了严重的支气管扩张或淋巴瘤而最终死亡。因此指南建议免疫球蛋白替代疗法的起始量为 0.4~0.6 g/kg,每个月 1 次静脉滴注[16],合并支气管扩张者主张给予较高剂量的的免疫球蛋白治疗[6]。预防性使用抗体和保护性隔离对 CVID 患者有益处[17]。如患者合并细胞免疫功能缺陷,需注意禁用活疫苗。
如能早期诊断并适当治疗,患者预后较好[6]。死因多为难以控制的肺部感染或并发淋巴瘤或实体瘤。
3 讨论
本例患者既往多年“肺部感染”病史,多次胸部 CT 均提示支气管扩张,且反复使用抗生素效果不佳,后期逐渐发展为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结合患者相关检查,符合诊断标准中的 ABC 及部分 D 条目,达到拟诊 CVID 标准。因此,考虑本例患者为 CVID 合并细胞免疫缺陷导致支气管扩张、肝硬化、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但仔细阅读患者胸部 CT 可发现,患者双肺仅部分支气管扩张、管壁增厚,其病变范围和程度与慢性肺源性心脏病严重程度不完全一致。且肺功能提示该患者除重度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外,同时存在严重弥散功能降低,无法完全用支气管扩张解释。分析其原因可能为:第一,由于患者存在支气管扩张、管壁增厚,用力肺活量降低,导致 V/Q 比例失调;第二,该例属少见的肝脏受累患者,既往研究表明肝硬化的存在可以使肝脏对循环中肺血管舒张因子的清除功能以及对门静脉中多种血管活性因子的代谢功能丧失[18],由此可致肺内血管扩张,V/Q 比例失调。这两方面原因可解释患者严重低氧血症、肺动脉高压及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因此,本例患者的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的原因除了反复感染所致的支气管扩张外,还与 CVID 肝脏受累导致肺通气血流比失调有关。
此外,本例患者还同时合并有外周血 CD4+T 细胞绝对计数、CD4/CD8 比例下降,骨髓流式细胞学提示 CD4+T 细胞占比下降。提示该患者同时存在细胞免疫功能缺陷。Takahashi 等[19]和 Malphettes 等[20]报道部分 CVID 患者可以同时合并细胞免疫功能缺陷,其机制可能与 T 细胞对分裂素和抗原刺激的反应下降及凋亡增加相关[21]。这也是本例患者频繁发生肺部感染的原因之一。
在本例患者在长达 20 余年的病程中,反复诊断为肺部感染并给予抗感染治疗。但病情仍频繁发生,近 1 年患者几乎每个月均需无间断地接受静脉注射抗生素治疗。在既往整个诊治过程,从未对其反复发生肺部感染的原因进行筛查。此次诊断明确后给予免疫球蛋白治疗,患者出院后 1 个月未再发生肺部感染及使用抗生素。因此明确诊断并及时治疗是控制本病的关键。基于这一疾病缺乏特异性症状、难发现、易误漏诊的特点,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原发性免疫缺陷病基金会提出了 CVID 的预警症状包括:一年中有 8 次或 8 次以上的中耳炎,2 次或 2 次以上的严重鼻窦炎、肺炎、非常见部位感染,反复发生的深部皮肤或脏器感染,非常见或条件性致病菌感染以及家族中有原发性免疫缺陷病病史者[22]。因此,临床中对于反复发生的感染且治疗效果较差时需高度警惕该病的可能并注意鉴别诊断,避免漏诊或仅诊断为免疫功能低下而停止进一步病因的深究,以致患者不能得到及时诊断及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