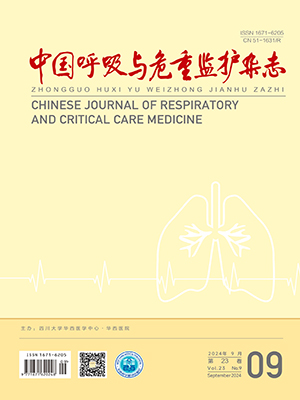引用本文: 陈佳怡, 梁宗安. 基于肺癌分类标准演变对肺炎型肺癌的新认识.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18, 17(6): 633-638. doi: 10.7507/1671-6205.201803021 复制
肺癌是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1],是全球范围内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国卫生经济负担最重的癌症[2]。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占肺癌总数的 80%~85%[3],其中肺腺癌已成为最常见的病理类型。部分肺腺癌在影像学上与各种类型的肺炎或间质性肺疾病相似,常表现未斑片或大片状、磨玻璃影、网格状阴影等,而肺结构和容积则较少改变,临床上称之为肺炎型肺癌(pneumonic-type of adenocarcinoma)。既往认为肺炎型肺癌是一种以贴壁生长(lepidic growth)为主的混合性细支气管肺泡癌(mixed bronchioloalveolar carcinoma,BAC),按其分布特点又称为弥漫性 BAC(diffuse pneumonic BAC),与其他类型的 BAC 相比,预后更差。2011 年的肺癌分类标准取消了 BAC 的命名,对肺炎型肺癌中侵袭成分的评估更为细致,概念上,肺炎型肺癌属于浸润性腺癌,后者范围更大。临床表现上,肺炎型肺癌缺乏特异性症状和体征,咳大量黏痰是部分患者晚期的特征表现。肺炎型肺癌在取得病理前容易误诊,确诊时多已失去手术机会,对化疗似乎也欠敏感,靶向药物则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本文结合国际上肺腺癌分类标准的演变对肺炎型肺癌进行阐述,以加深对其思考和认识。
1 定义和流行病学
1.1 BAC 命名的困惑
肺炎型肺癌的描述由来已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肺炎型肺癌的概念和 BAC 关系密切。1999/2004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类标准将 BAC 定义为一种不侵及基质、胸膜和血管,肿瘤细胞沿肺泡和细支气管壁匍匐生长即贴壁生长的肺癌。基于该分类标准,大部分肺炎型肺癌的病理是混合性 BAC,病灶中还包含黏液细胞、不典型增生、浸润性腺癌等多种成分[4]。然而,这一定义出现后,有学者对既往诊断过 BAC 的患者进行重新评估和分类,发现临床上由于对“肺炎样”病灶的全貌认识不足,容易低估病灶的侵袭成分,而过度使用 BAC 这一命名,给临床诊疗和预后评价造成混乱,也给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带来困难[5]。Zell 等[6]回顾分析了 626 例 BAC 病例,发现 1999 年 5 月后确诊 BAC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OS)显著长于之前诊断的患者(>53 个月比 32 个月,P=0.012),而这种改善归功于对 WHO 对 BAC 的严格定义。所以人们对 BAC 的使用越来越谨慎,要求临床实践中有足够且全面的标本检查,在小标本中即使是纯贴壁生长,也不能否认浸润成分的存在。
1.2 新分类标准下的肺炎型肺癌
直到 2011 年国际肺癌研究协会/美国胸科学会/欧洲呼吸学会(IASLC/ATS/ERS)联合公布的肺腺癌的国际多学科分类标准和 2015 年 WHO 肺腺癌病理分型,均弃用了 BAC 这一术语,而代之以对肿瘤大小及浸润程度更细化的原位腺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AIS)、微浸润腺癌(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MIA)等名词。浸润性腺癌或称侵袭性腺癌(invasive adenocarcinoma)则按主要的组织学亚型命名,浸润的定义即肿瘤呈腺泡状、乳头状、微乳头状和实性生长并且浸润间质、胸膜或发生播散,若以贴壁生长为主则分类为贴壁生长为主的腺癌(lepidic predominant adenocarcinoma,LPA)[7]。非黏液型 BAC 细分为 AIS、MIA、LPA,黏液型 BAC 细分为黏液型 AIS 和浸润性黏液腺癌。
废除 BAC 削弱了临床对磨玻璃/贴壁(ground glass/lepidic,GG/L)成分的过分关注,肺炎型肺癌的侵袭性和恶性程度被重视。根据 IASLC 分期及预后委员会推荐[8],临床标准要求肿瘤呈现“肺炎样”的区域病变:(1)不论融合性或多发性区域;(2)可表现为磨玻璃影、实变或两者混合;(3)高度怀疑恶性病变的区域可包含在内,不管该区域是否经过活检;(4)不适用于多发离散型结节;(5)不适用于肿瘤堵塞支气管引起的肺炎和肺不张。病理标准要求肿瘤在肺内某一区域呈弥漫性分布,而非边缘清晰的孤立肿块或多发结节:(1)典型的病理为浸润性黏液腺癌,非黏液型和混合黏液型也可存在;(2)肿瘤细胞以贴壁样生长为主,可含有腺泡样、乳头状、微乳头状等混杂成分。
1.3 流行病学
由于缺乏统一的定义和分类标准,肺炎型肺癌的人口学资料十分有限。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监测流行病学数据库显示,1973~2002 年所有类型 BAC 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66.99 岁[9],相比之下,肺炎型肺癌发病似乎更年轻,平均年龄在 41~66 岁[8]。女性和不吸烟者在 BAC 中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也有研究报道在年龄、性别、吸烟状况方面 BAC 和其他形式肺癌并无明显差异[10]。
2 病因学
目前普遍认为肺癌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的影响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11]。肺腺癌和 BAC 的病因研究仍显示出一些独特之处,例如,和其他类型的肺癌相比非吸烟者比例较高,更有学者认为 BAC 与吸烟关系不大[12]。环境致癌颗粒或烟尘暴露是肺腺癌发病的重要因素,包括石棉[13]、室内氡气[14]、烟煤[15]、木材燃烧产物[16-18]等,这些暴露也是我国非吸烟女性肺癌比例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19]。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厨房油烟是女性肺癌的危险因素,且与吸烟状况无关[20]。此外,Yang 等[21]回顾相关文献,总结了 153 例结缔组织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CTD)合并肺癌的情况,发现肺癌合并系统性硬化症最多,BAC(25.5%)和腺癌(23.5%)是最多见的病理类型。多发性肌炎/皮肌炎(polymyositis/dermatomyositis,PM/DM)可合并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腺癌是除血液系统肿瘤外所有原发肿瘤最多见的病理类型[22],也有学者将 PM/DM 视为一种副肿瘤综合征[23]。雌激素促进肺癌发生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有研究发现肺腺癌组织中的雌激素受体表达水平增高,且 EGFR 途径与雌激素信号传导之间存在相互作用[24],因此,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和抗雌激素的联合治疗开始被评估[25]。
3 临床表现
肺炎型肺癌在临床表现上无特异性,早期仅有咳嗽、咳痰,随着病情进展出现咳大量黏痰、呼吸困难、低氧血症、胸痛等,经抗感染、抗结核、糖皮质激素治疗常常无效或加重,CT 动态观察出现病灶增多、密度变实。也有学者认为,咳大量白黏痰是肺炎型肺癌晚期特征表现,称之为支气管溢液(每日痰量>100 ml)。大量黏液填充支气管及肺泡,引起肺内分流导致严重低氧血症、呼吸困难,是黏液型腺癌预后更差的重要原因[26-28]。
4 组织病理和影像学特征
4.1 肺炎型肺癌的病理进展和分子机制
肺炎型肺癌的病理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认为,肺腺癌最常见的起源和进展途径是从正常组织-不典型增生(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AAH)-AIS-MIA-LPA,再到成分更复杂的浸润性腺癌,这一过程有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上的特点和规律[29]。肿瘤细胞主要起源于 Clara 细胞、Ⅱ型肺泡上皮细胞,细胞核大小不一,多位于基底部,电镜下还可发现细胞顶端分布卵圆形或不规则包膜颗粒[30]。少数黏液型肿瘤细胞则呈高柱状或高脚杯状,细胞异型性并不明显[31-32]。AAH 在 CT 上显示为很小(小于 0.5 cm)的 GGO,显微镜下不典型增生的肺泡细胞沿着肺泡壁延伸,可认为是肿瘤贴壁生长的来源。AIS 和 MIA 通常直径≤3 cm,显微镜下的 AIS 核异质细胞单纯贴壁生长,MIA 则开始出现不同形态的侵袭成分(≤5 mm),但 MIA 很少侵及血管、淋巴管、胸膜或发生坏死和播散,完全切除后两者的 5 年生存率均可达 100%。随着侵袭成分进一步增大,大部分非黏液型 AIS 和 MIA 进展为 LPA,三者在临床上有时难以鉴别,但 LPA 已显示出更差的预后[29]。极少数黏液型肿瘤则进展为浸润性黏液腺癌,即肺炎型肺癌的常见病理类型。在肺炎型肺癌的病理分析中,“肺炎样”特征来源于贴壁成分迅速增殖,而浸润灶的细胞组分复杂多样并常见黏液细胞[31-32]。此外,有观点认为多原发 GG/L 结节是肺炎型肺癌的前期状态,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特殊形式[8, 33],我们在临床中观察到了这一过程(图 1),说明肺炎型肺癌形成机制可能更为复杂。该患者为 45 岁的男性,车间工人,因“咳大量黏痰、呼吸困难 2 个月”就诊,按肺炎治疗 1 个月未见好转,经皮肺穿刺活检示中分化腺癌,免疫组化检查提示其 PDL1、ROS1 和 ALK-V/D5F 均为阴性,全身核素骨显像和全腹及头部增强 CT 未见异常,最终确诊为右肺中分化腺癌伴双肺广泛转移及纵隔淋巴结转移(T4N2M1a Ⅳ期)。
 图1
不同时间点肺炎型肺癌患者的胸部CT像
图1
不同时间点肺炎型肺癌患者的胸部CT像
a. 2016 年 7 月,双肺多发斑片、磨玻璃、条索影;b. 2016 年 9 月,磨玻璃、实变影扩大融合,内可见支气管充气征;c. 2016 年10 月病灶继续进展
分子生物学方面,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er,EGFR)、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KRAS)、鼠类肉瘤滤过性毒菌(v-Raf)致癌同源体 B1(v-Raf murine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B1,BRAF)突变可诱导正常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增殖和异型化并进展为 AAH。之后,EGFR 继续扩增促使 EGFR 突变型 AAH 向 AIS 和浸润性腺癌发展。KRAS 或 BRAF 突变型 AAH 却似乎很少进展为侵袭性病变,可能与癌基因诱导细胞衰老和表观遗传改变有关,但抑癌基因 TP53/CDKN2A 失活等分子事件仍可导致肿瘤继续进展[29]。此外,差异也存在于黏液型和非黏液型腺癌中,如 Garfield 等[32]回顾文献发现,在黏液型和非黏液型的 BAC 中,细胞角蛋白-20(cytokeratin-20,CK-20)阳性率分别为 53% 和 3%,甲状腺核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阳性率为 24% 和 88%,EGFR 突变率为 3% 和 45%,KRAS 突变率为 34% 和 14%。也有研究显示 KRAS 突变是黏液型腺癌最常见的基因驱动,且和非黏液型的突变类型不同[31]。
4.2 肺炎型肺癌的影像特征及病理依据
肺炎型肺癌在胸部 CT 上表现出磨玻璃影、大片实变或斑片影、支气管扩张、网格状、条索状阴影、支气管充气征等,这种“肺炎样”表现和肿瘤的病理特征密切相关。影像学与病理表现的关系体现在:(1)肿瘤细胞沿气道、肺泡的匍匐生长,气腔内被黏液分泌和瘤结节填充,同时也存在炎性浸润和纤维增殖病变,CT 上表现为 GGO 病灶增多、范围增大、实体化和融合改变,但较少形成空洞液化[31];(2)支气管在实变背景中形成支气管充气征,受到肿瘤组织牵拉、压迫、增殖可出现气道僵直、粗细不均、分支角度增大、内壁结节等[34];(3)肿瘤沿淋巴道蔓延形成癌性淋巴管炎和间质水肿,表现为网织状肺纹理和肺血管束变形、僵直[28];(4)病灶中的侵袭成分隐蔽在炎性背景中形成结节、肿块影;(5)增强 CT 上,肺动静脉清晰显示在实变背景下,病灶内血管影变细或扭曲变形;(6)叶间裂膨出往往提示增殖性病变;(7)“假空洞征”即实变病灶内出现空泡或蜂窝状透亮影,是由于肿瘤细胞及黏液阻塞引起的局限肺气肿,而非病灶坏死引流所致。值得注意的是,CT 对肺炎性肺癌的评价也有不足之处,一项研究分析了 88 例肺腺癌的胸部 CT 和手术标本,在多灶性腺癌中,CT 检出所有病变区域的敏感性欠佳,两名影像医师分别为 0.63 和 0.68[35]。另有学者认为,CT 上“肺炎样”区域超过单肺叶者,其显微镜下病理检查更有可能累及双肺[36]。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C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上肺炎型肺癌多呈大片状代谢增高影,内含更高代谢病灶,CT 上表现为磨玻璃影的区域 SUV 值往往低于实性成分,甚至纯磨玻璃影可出现假阴性结果,间接说明肿瘤成分复杂,代谢需求不同。也有研究发现分泌黏液较多的病灶也可出现低摄取,或假阴性结果[37]。
肺炎型肺癌的 TNM 分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第八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分期建议肺炎型肺癌依然根据肿瘤大小分期,当无法确定肿瘤大小但病灶局限于单肺叶时归为 T3,累及同侧其他肺叶时为 T4,累及双肺时为 M1a[4, 38]。临床观察到部分肺炎型肺癌即使有广泛的肺内转移,淋巴结和远处转移也相对较晚,使得的分期评价呈现出 N0M1 概率较高的特点[28, 39]。
5 诊断和评估
组织病理是肺癌诊断的唯一金标准,选择合适的取材方式更有利于获得理想的结果。细胞学检查和病理科医生的经验及主观判断有较大联系,总体来说阳性率较低。由于肺炎型肺癌为外周型居多,经支气管镜检多不易查见黏膜异常或新生肿物等,在此的基础上一些新技术如电磁导航支气管镜、超声支气管镜等新技术的开展有望提高肺癌的诊断效能。有文献报道肺炎型肺癌支气管镜检查总体阳性率为 80.8%[28],支气管镜检查阴性的患者,大多通过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或外科手段等方法,选择 CT 影像中实性或结节区域,必要时重复多点穿刺。另外,免疫组化和基因检测肿瘤的病理诊断更精准和完善。目前对于腺癌或含腺癌成分的其他类型肺癌,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指南和国内共识均要求常规进行 EGFR 基因突变和 ALK 融合基因检测,此外很多机构建议同时进行 ROS、RET、MET 原癌基因、BRAF 和 HER2 筛查,对应的靶向药物治疗前景也被众多学者看好。近年来,基于外周血中循环肿瘤 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以及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s)的基因分析使得基因检测更加便利。研究表明,在监测接受靶向治疗的 EGFR 突变患者的治疗反应,以及是否存在 T790M 耐药突变方面,ct-DNA 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前景[40]。
6 治疗及预后
与其他类型的肺癌一样,肺炎型肺癌的治疗应根据其临床分期和病理类型选择综合性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临床分期和是否有条件接受根治性手术是决定肺癌预后的重要因素。肺炎型肺癌因肿瘤范围广常常被认为无手术指征而接受内科治疗[41]。虽然 TNM 分期已属于晚期,但由于贴壁癌细胞的生物学特点,使得肺炎型肺癌倾向于首先肺内播散,有限的临床数据提示外科手术在这类患者中可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42-43]。也是由于 BAC 的相对惰性和不易肺外转移,有学者认为一定条件下肺移植也是一种可尝试的治疗方法[44]。但至今,肺炎型肺癌的手术指征和意义还需严格探讨。少量研究显示,化疗对晚期 BAC 患者并未显示出较其他类型肺腺癌更积极的意义,肺炎型肺癌对紫杉醇化疗的敏感性低于其他类型的 NSCLC[45],另有报道培美曲塞将晚期肺炎型肺癌总生存率延长至 23 个月[46],其他化疗药物联合培美曲塞为肺炎型肺癌化疗选择提供了更多参考[47]。目前大量研究证实 EGFR-TKI 一线治疗 EGFR 突变阳性的晚期 NSCLC 优于化疗[48],非黏液性腺癌 EGFR 突变率较高,阳性率可达 45%,而浸润性肺黏液腺癌 EGFR 突变率绝大多数为阴性,阳性率仅 3%[49]。
预后方面,一些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和肺炎型肺癌更差的预后相关,包括气腔内播散(spread through air space,STAS)、支气管溢液、细湿啰音、多病灶、多肺叶或双肺病灶等[26]。另一项研究分析了 707 例晚期 BAC 患者的预后,仅有单侧肺内转移较其他类型有更长的生存期(ⅢB 期>58 个月比 10 个月,P<0.000 1,Ⅳ期 15 个月比 7 个月,P=0.000 1)[50]。与多发的 GG/L 结节相比,弥漫型肺炎型肺癌的预后更差[41, 43]。病理学上,黏液型较非黏液型腺癌预后差[51],这和上述研究中显示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预后规律相一致。通常认为,肺炎型肺癌患者死亡主要归因于肺内肿瘤负荷引起的呼吸衰竭,而非远处转移。
7 结语
肺炎型肺癌并不是国际肺癌分类中的一个亚型,过去 BAC 在显微镜下的非侵袭性似乎让临床医生感到兴奋,然而,按照目前的认识,即使病灶以贴壁生长为主,>3 cm 的病灶已经极大可能有更强的侵袭性。肺炎型肺癌病变广预后差,对其浸润成分的评估绝不能掉以轻心。此外,针对肺炎型肺癌和 BAC 的研究长期存在纳入标准参差不齐、概念混用的问题,即使在 2011 年后的研究中仍不乏使用 BAC 的概念,研究者采用 diffuse pneumonic BAC/adenocarcinoma、mixed BAC 等表述,因此需要进一步统一标准来助力高质量研究的开展。当然,目前对于肺炎型肺癌仍知之甚少,有待于更深入了解其生物学行为和分子生物学全貌,从而帮助临床医生制定更合理的治疗策略。
肺癌是目前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1],是全球范围内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国卫生经济负担最重的癌症[2]。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占肺癌总数的 80%~85%[3],其中肺腺癌已成为最常见的病理类型。部分肺腺癌在影像学上与各种类型的肺炎或间质性肺疾病相似,常表现未斑片或大片状、磨玻璃影、网格状阴影等,而肺结构和容积则较少改变,临床上称之为肺炎型肺癌(pneumonic-type of adenocarcinoma)。既往认为肺炎型肺癌是一种以贴壁生长(lepidic growth)为主的混合性细支气管肺泡癌(mixed bronchioloalveolar carcinoma,BAC),按其分布特点又称为弥漫性 BAC(diffuse pneumonic BAC),与其他类型的 BAC 相比,预后更差。2011 年的肺癌分类标准取消了 BAC 的命名,对肺炎型肺癌中侵袭成分的评估更为细致,概念上,肺炎型肺癌属于浸润性腺癌,后者范围更大。临床表现上,肺炎型肺癌缺乏特异性症状和体征,咳大量黏痰是部分患者晚期的特征表现。肺炎型肺癌在取得病理前容易误诊,确诊时多已失去手术机会,对化疗似乎也欠敏感,靶向药物则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本文结合国际上肺腺癌分类标准的演变对肺炎型肺癌进行阐述,以加深对其思考和认识。
1 定义和流行病学
1.1 BAC 命名的困惑
肺炎型肺癌的描述由来已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肺炎型肺癌的概念和 BAC 关系密切。1999/2004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类标准将 BAC 定义为一种不侵及基质、胸膜和血管,肿瘤细胞沿肺泡和细支气管壁匍匐生长即贴壁生长的肺癌。基于该分类标准,大部分肺炎型肺癌的病理是混合性 BAC,病灶中还包含黏液细胞、不典型增生、浸润性腺癌等多种成分[4]。然而,这一定义出现后,有学者对既往诊断过 BAC 的患者进行重新评估和分类,发现临床上由于对“肺炎样”病灶的全貌认识不足,容易低估病灶的侵袭成分,而过度使用 BAC 这一命名,给临床诊疗和预后评价造成混乱,也给相关流行病学研究带来困难[5]。Zell 等[6]回顾分析了 626 例 BAC 病例,发现 1999 年 5 月后确诊 BAC 患者的中位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OS)显著长于之前诊断的患者(>53 个月比 32 个月,P=0.012),而这种改善归功于对 WHO 对 BAC 的严格定义。所以人们对 BAC 的使用越来越谨慎,要求临床实践中有足够且全面的标本检查,在小标本中即使是纯贴壁生长,也不能否认浸润成分的存在。
1.2 新分类标准下的肺炎型肺癌
直到 2011 年国际肺癌研究协会/美国胸科学会/欧洲呼吸学会(IASLC/ATS/ERS)联合公布的肺腺癌的国际多学科分类标准和 2015 年 WHO 肺腺癌病理分型,均弃用了 BAC 这一术语,而代之以对肿瘤大小及浸润程度更细化的原位腺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AIS)、微浸润腺癌(minimally invasive adenocarcinoma,MIA)等名词。浸润性腺癌或称侵袭性腺癌(invasive adenocarcinoma)则按主要的组织学亚型命名,浸润的定义即肿瘤呈腺泡状、乳头状、微乳头状和实性生长并且浸润间质、胸膜或发生播散,若以贴壁生长为主则分类为贴壁生长为主的腺癌(lepidic predominant adenocarcinoma,LPA)[7]。非黏液型 BAC 细分为 AIS、MIA、LPA,黏液型 BAC 细分为黏液型 AIS 和浸润性黏液腺癌。
废除 BAC 削弱了临床对磨玻璃/贴壁(ground glass/lepidic,GG/L)成分的过分关注,肺炎型肺癌的侵袭性和恶性程度被重视。根据 IASLC 分期及预后委员会推荐[8],临床标准要求肿瘤呈现“肺炎样”的区域病变:(1)不论融合性或多发性区域;(2)可表现为磨玻璃影、实变或两者混合;(3)高度怀疑恶性病变的区域可包含在内,不管该区域是否经过活检;(4)不适用于多发离散型结节;(5)不适用于肿瘤堵塞支气管引起的肺炎和肺不张。病理标准要求肿瘤在肺内某一区域呈弥漫性分布,而非边缘清晰的孤立肿块或多发结节:(1)典型的病理为浸润性黏液腺癌,非黏液型和混合黏液型也可存在;(2)肿瘤细胞以贴壁样生长为主,可含有腺泡样、乳头状、微乳头状等混杂成分。
1.3 流行病学
由于缺乏统一的定义和分类标准,肺炎型肺癌的人口学资料十分有限。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监测流行病学数据库显示,1973~2002 年所有类型 BAC 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66.99 岁[9],相比之下,肺炎型肺癌发病似乎更年轻,平均年龄在 41~66 岁[8]。女性和不吸烟者在 BAC 中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也有研究报道在年龄、性别、吸烟状况方面 BAC 和其他形式肺癌并无明显差异[10]。
2 病因学
目前普遍认为肺癌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因素的影响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11]。肺腺癌和 BAC 的病因研究仍显示出一些独特之处,例如,和其他类型的肺癌相比非吸烟者比例较高,更有学者认为 BAC 与吸烟关系不大[12]。环境致癌颗粒或烟尘暴露是肺腺癌发病的重要因素,包括石棉[13]、室内氡气[14]、烟煤[15]、木材燃烧产物[16-18]等,这些暴露也是我国非吸烟女性肺癌比例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19]。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厨房油烟是女性肺癌的危险因素,且与吸烟状况无关[20]。此外,Yang 等[21]回顾相关文献,总结了 153 例结缔组织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CTD)合并肺癌的情况,发现肺癌合并系统性硬化症最多,BAC(25.5%)和腺癌(23.5%)是最多见的病理类型。多发性肌炎/皮肌炎(polymyositis/dermatomyositis,PM/DM)可合并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腺癌是除血液系统肿瘤外所有原发肿瘤最多见的病理类型[22],也有学者将 PM/DM 视为一种副肿瘤综合征[23]。雌激素促进肺癌发生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但有研究发现肺腺癌组织中的雌激素受体表达水平增高,且 EGFR 途径与雌激素信号传导之间存在相互作用[24],因此,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TKIs)和抗雌激素的联合治疗开始被评估[25]。
3 临床表现
肺炎型肺癌在临床表现上无特异性,早期仅有咳嗽、咳痰,随着病情进展出现咳大量黏痰、呼吸困难、低氧血症、胸痛等,经抗感染、抗结核、糖皮质激素治疗常常无效或加重,CT 动态观察出现病灶增多、密度变实。也有学者认为,咳大量白黏痰是肺炎型肺癌晚期特征表现,称之为支气管溢液(每日痰量>100 ml)。大量黏液填充支气管及肺泡,引起肺内分流导致严重低氧血症、呼吸困难,是黏液型腺癌预后更差的重要原因[26-28]。
4 组织病理和影像学特征
4.1 肺炎型肺癌的病理进展和分子机制
肺炎型肺癌的病理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目前认为,肺腺癌最常见的起源和进展途径是从正常组织-不典型增生(atypical adenomatous hyperplasia,AAH)-AIS-MIA-LPA,再到成分更复杂的浸润性腺癌,这一过程有病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上的特点和规律[29]。肿瘤细胞主要起源于 Clara 细胞、Ⅱ型肺泡上皮细胞,细胞核大小不一,多位于基底部,电镜下还可发现细胞顶端分布卵圆形或不规则包膜颗粒[30]。少数黏液型肿瘤细胞则呈高柱状或高脚杯状,细胞异型性并不明显[31-32]。AAH 在 CT 上显示为很小(小于 0.5 cm)的 GGO,显微镜下不典型增生的肺泡细胞沿着肺泡壁延伸,可认为是肿瘤贴壁生长的来源。AIS 和 MIA 通常直径≤3 cm,显微镜下的 AIS 核异质细胞单纯贴壁生长,MIA 则开始出现不同形态的侵袭成分(≤5 mm),但 MIA 很少侵及血管、淋巴管、胸膜或发生坏死和播散,完全切除后两者的 5 年生存率均可达 100%。随着侵袭成分进一步增大,大部分非黏液型 AIS 和 MIA 进展为 LPA,三者在临床上有时难以鉴别,但 LPA 已显示出更差的预后[29]。极少数黏液型肿瘤则进展为浸润性黏液腺癌,即肺炎型肺癌的常见病理类型。在肺炎型肺癌的病理分析中,“肺炎样”特征来源于贴壁成分迅速增殖,而浸润灶的细胞组分复杂多样并常见黏液细胞[31-32]。此外,有观点认为多原发 GG/L 结节是肺炎型肺癌的前期状态,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特殊形式[8, 33],我们在临床中观察到了这一过程(图 1),说明肺炎型肺癌形成机制可能更为复杂。该患者为 45 岁的男性,车间工人,因“咳大量黏痰、呼吸困难 2 个月”就诊,按肺炎治疗 1 个月未见好转,经皮肺穿刺活检示中分化腺癌,免疫组化检查提示其 PDL1、ROS1 和 ALK-V/D5F 均为阴性,全身核素骨显像和全腹及头部增强 CT 未见异常,最终确诊为右肺中分化腺癌伴双肺广泛转移及纵隔淋巴结转移(T4N2M1a Ⅳ期)。
 图1
不同时间点肺炎型肺癌患者的胸部CT像
图1
不同时间点肺炎型肺癌患者的胸部CT像
a. 2016 年 7 月,双肺多发斑片、磨玻璃、条索影;b. 2016 年 9 月,磨玻璃、实变影扩大融合,内可见支气管充气征;c. 2016 年10 月病灶继续进展
分子生物学方面,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er,EGFR)、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KRAS)、鼠类肉瘤滤过性毒菌(v-Raf)致癌同源体 B1(v-Raf murine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B1,BRAF)突变可诱导正常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增殖和异型化并进展为 AAH。之后,EGFR 继续扩增促使 EGFR 突变型 AAH 向 AIS 和浸润性腺癌发展。KRAS 或 BRAF 突变型 AAH 却似乎很少进展为侵袭性病变,可能与癌基因诱导细胞衰老和表观遗传改变有关,但抑癌基因 TP53/CDKN2A 失活等分子事件仍可导致肿瘤继续进展[29]。此外,差异也存在于黏液型和非黏液型腺癌中,如 Garfield 等[32]回顾文献发现,在黏液型和非黏液型的 BAC 中,细胞角蛋白-20(cytokeratin-20,CK-20)阳性率分别为 53% 和 3%,甲状腺核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TTF-1)阳性率为 24% 和 88%,EGFR 突变率为 3% 和 45%,KRAS 突变率为 34% 和 14%。也有研究显示 KRAS 突变是黏液型腺癌最常见的基因驱动,且和非黏液型的突变类型不同[31]。
4.2 肺炎型肺癌的影像特征及病理依据
肺炎型肺癌在胸部 CT 上表现出磨玻璃影、大片实变或斑片影、支气管扩张、网格状、条索状阴影、支气管充气征等,这种“肺炎样”表现和肿瘤的病理特征密切相关。影像学与病理表现的关系体现在:(1)肿瘤细胞沿气道、肺泡的匍匐生长,气腔内被黏液分泌和瘤结节填充,同时也存在炎性浸润和纤维增殖病变,CT 上表现为 GGO 病灶增多、范围增大、实体化和融合改变,但较少形成空洞液化[31];(2)支气管在实变背景中形成支气管充气征,受到肿瘤组织牵拉、压迫、增殖可出现气道僵直、粗细不均、分支角度增大、内壁结节等[34];(3)肿瘤沿淋巴道蔓延形成癌性淋巴管炎和间质水肿,表现为网织状肺纹理和肺血管束变形、僵直[28];(4)病灶中的侵袭成分隐蔽在炎性背景中形成结节、肿块影;(5)增强 CT 上,肺动静脉清晰显示在实变背景下,病灶内血管影变细或扭曲变形;(6)叶间裂膨出往往提示增殖性病变;(7)“假空洞征”即实变病灶内出现空泡或蜂窝状透亮影,是由于肿瘤细胞及黏液阻塞引起的局限肺气肿,而非病灶坏死引流所致。值得注意的是,CT 对肺炎性肺癌的评价也有不足之处,一项研究分析了 88 例肺腺癌的胸部 CT 和手术标本,在多灶性腺癌中,CT 检出所有病变区域的敏感性欠佳,两名影像医师分别为 0.63 和 0.68[35]。另有学者认为,CT 上“肺炎样”区域超过单肺叶者,其显微镜下病理检查更有可能累及双肺[36]。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C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上肺炎型肺癌多呈大片状代谢增高影,内含更高代谢病灶,CT 上表现为磨玻璃影的区域 SUV 值往往低于实性成分,甚至纯磨玻璃影可出现假阴性结果,间接说明肿瘤成分复杂,代谢需求不同。也有研究发现分泌黏液较多的病灶也可出现低摄取,或假阴性结果[37]。
肺炎型肺癌的 TNM 分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第八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分期建议肺炎型肺癌依然根据肿瘤大小分期,当无法确定肿瘤大小但病灶局限于单肺叶时归为 T3,累及同侧其他肺叶时为 T4,累及双肺时为 M1a[4, 38]。临床观察到部分肺炎型肺癌即使有广泛的肺内转移,淋巴结和远处转移也相对较晚,使得的分期评价呈现出 N0M1 概率较高的特点[28, 39]。
5 诊断和评估
组织病理是肺癌诊断的唯一金标准,选择合适的取材方式更有利于获得理想的结果。细胞学检查和病理科医生的经验及主观判断有较大联系,总体来说阳性率较低。由于肺炎型肺癌为外周型居多,经支气管镜检多不易查见黏膜异常或新生肿物等,在此的基础上一些新技术如电磁导航支气管镜、超声支气管镜等新技术的开展有望提高肺癌的诊断效能。有文献报道肺炎型肺癌支气管镜检查总体阳性率为 80.8%[28],支气管镜检查阴性的患者,大多通过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术或外科手段等方法,选择 CT 影像中实性或结节区域,必要时重复多点穿刺。另外,免疫组化和基因检测肿瘤的病理诊断更精准和完善。目前对于腺癌或含腺癌成分的其他类型肺癌,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指南和国内共识均要求常规进行 EGFR 基因突变和 ALK 融合基因检测,此外很多机构建议同时进行 ROS、RET、MET 原癌基因、BRAF 和 HER2 筛查,对应的靶向药物治疗前景也被众多学者看好。近年来,基于外周血中循环肿瘤 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以及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s)的基因分析使得基因检测更加便利。研究表明,在监测接受靶向治疗的 EGFR 突变患者的治疗反应,以及是否存在 T790M 耐药突变方面,ct-DNA 具有很好的临床应用前景[40]。
6 治疗及预后
与其他类型的肺癌一样,肺炎型肺癌的治疗应根据其临床分期和病理类型选择综合性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临床分期和是否有条件接受根治性手术是决定肺癌预后的重要因素。肺炎型肺癌因肿瘤范围广常常被认为无手术指征而接受内科治疗[41]。虽然 TNM 分期已属于晚期,但由于贴壁癌细胞的生物学特点,使得肺炎型肺癌倾向于首先肺内播散,有限的临床数据提示外科手术在这类患者中可取得一定的治疗效果[42-43]。也是由于 BAC 的相对惰性和不易肺外转移,有学者认为一定条件下肺移植也是一种可尝试的治疗方法[44]。但至今,肺炎型肺癌的手术指征和意义还需严格探讨。少量研究显示,化疗对晚期 BAC 患者并未显示出较其他类型肺腺癌更积极的意义,肺炎型肺癌对紫杉醇化疗的敏感性低于其他类型的 NSCLC[45],另有报道培美曲塞将晚期肺炎型肺癌总生存率延长至 23 个月[46],其他化疗药物联合培美曲塞为肺炎型肺癌化疗选择提供了更多参考[47]。目前大量研究证实 EGFR-TKI 一线治疗 EGFR 突变阳性的晚期 NSCLC 优于化疗[48],非黏液性腺癌 EGFR 突变率较高,阳性率可达 45%,而浸润性肺黏液腺癌 EGFR 突变率绝大多数为阴性,阳性率仅 3%[49]。
预后方面,一些临床和影像学特征和肺炎型肺癌更差的预后相关,包括气腔内播散(spread through air space,STAS)、支气管溢液、细湿啰音、多病灶、多肺叶或双肺病灶等[26]。另一项研究分析了 707 例晚期 BAC 患者的预后,仅有单侧肺内转移较其他类型有更长的生存期(ⅢB 期>58 个月比 10 个月,P<0.000 1,Ⅳ期 15 个月比 7 个月,P=0.000 1)[50]。与多发的 GG/L 结节相比,弥漫型肺炎型肺癌的预后更差[41, 43]。病理学上,黏液型较非黏液型腺癌预后差[51],这和上述研究中显示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预后规律相一致。通常认为,肺炎型肺癌患者死亡主要归因于肺内肿瘤负荷引起的呼吸衰竭,而非远处转移。
7 结语
肺炎型肺癌并不是国际肺癌分类中的一个亚型,过去 BAC 在显微镜下的非侵袭性似乎让临床医生感到兴奋,然而,按照目前的认识,即使病灶以贴壁生长为主,>3 cm 的病灶已经极大可能有更强的侵袭性。肺炎型肺癌病变广预后差,对其浸润成分的评估绝不能掉以轻心。此外,针对肺炎型肺癌和 BAC 的研究长期存在纳入标准参差不齐、概念混用的问题,即使在 2011 年后的研究中仍不乏使用 BAC 的概念,研究者采用 diffuse pneumonic BAC/adenocarcinoma、mixed BAC 等表述,因此需要进一步统一标准来助力高质量研究的开展。当然,目前对于肺炎型肺癌仍知之甚少,有待于更深入了解其生物学行为和分子生物学全貌,从而帮助临床医生制定更合理的治疗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