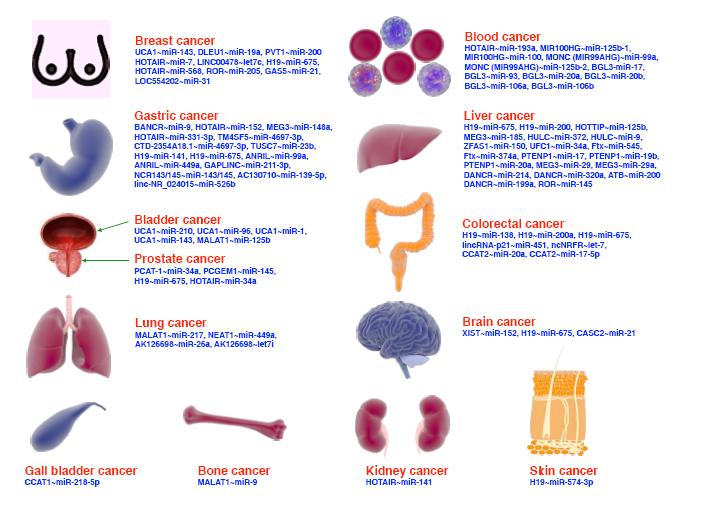2023年美国癌症协会统计显示,肺癌现为全世界发病率第2、死亡率第1的恶性肿瘤,其中约85%的肺癌病理类型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1]。依据分期来行手术和辅助治疗是NSCLC的主要治疗方案,早期NSCLC患者通过手术切除后10年生存率极高,但大多数患者确诊NSCLC已为局部晚期,预后较差。近些年,新辅助治疗已被证实能够显著改善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及无复发生存率(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2-5]。
而随着新辅助治疗在临床实践中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关于新辅助治疗后手术路径的争论也越来越多。新辅助治疗,特别是免疫治疗诱发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irAE)可能导致局部炎症,使胸膜和肺组织发生致密粘连,甚至纤维化[6]。这可能会增加手术视野的复杂性,因此手术路径选择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在早期NSCLC的切除术中,电视胸腔镜辅助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VATS)优于开胸手术,具有并发症少、疼痛轻、恢复快和长期生存率相当的优点[7-10];最近的研究[11-15]表明,NSCLC患者在新辅助化疗或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接受VATS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疗效。但这些报道基本为小样本,且多为新辅助化疗而关于其他新辅助治疗的报道较少,仍缺少NSCLC患者接受各种新辅助治疗后,VATS和开胸手术的对比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回顾性收集术前进行过新辅助治疗的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对NSCLC患者在接受新辅助治疗后手术的围手术期结果进行了初步探索,为NSCLC精准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本研究回顾性收集本院2020年6月—2022年5月NSCLC患者新辅助治疗后行VATS和开胸手术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术前行新辅助治疗(单药或联合用药)包括化疗、免疫疗法、靶向疗法。排除标准:(1)临床或影像学信息不完整;(2)既往有肺部手术史;(3)复发性NSCLC;(4)N3或远处转移;(5)术前放疗。
1.2 新辅助治疗及评价
所有纳入患者均行2~6周期新辅助治疗,其中化疗药物使用PP方案(培美曲塞+铂类)、TP方案(紫杉醇类+铂类)或者GP方案(吉西他滨+铂类)。免疫治疗药物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主要与化疗联合使用。靶向药物则根据患者驱动基因选择。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是指影像学上所有肿瘤靶病灶消失,无新病灶出现,且肿瘤标志物正常,至少维持4周。病理反应由上海市肺科医院病理科的专业人员进行评估。主要病理缓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MPR)定义为:在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的病理评估中,残留肿瘤细胞≤10%[16]。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定义为:在切除的肿瘤或切除的淋巴结中无证据表明有肿瘤细胞存活。NSCLC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分期采用美国癌症联合会第8版TNM分期系统,T分期中肿瘤大小调整为残存肿瘤的大小。N分期需要根据淋巴结内有无肿瘤细胞归入相应N分期。
1.3 手术治疗
经外科医师在内的多学科团队进行讨论,在新辅助治疗恢复后,将实施切除术。根据手术方法,患者被分为两组:VATS组:接受单孔或多孔胸腔镜手术患者;开胸手术组:接受传统开胸手术患者。所有患者均行根治性手术,切除肿瘤和阴性切缘(支气管、动脉、静脉、支气管周围、肿瘤附近组织),并清扫纵膈淋巴结。镜下切缘阴性为R0,镜下切缘阳性R1,肉眼可见肿瘤残余为R2[17]。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数据统计分析采用R软件(4.3.2版),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四格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则采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并采用两组比较的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分析。倾向性评分匹配使用matchit函数,卡钳值为0.2。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则采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并采用两组比较的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分析。倾向性评分匹配使用matchit函数,卡钳值为0.2。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规定,并通过上海市肺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K23-004;批准日期:2022年2月22日)。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特征
共纳入260例,男性占队列的71.9%,女性占队列28.1%。全部患者平均年龄(60.08±8.97)岁。114例患者(43.8%)确诊前未戒烟。主要组织学类型为腺癌(178例,68.5%)和鳞癌(70例,26.9%)。ASA评分都≤3分,大多为2分(89.6%)。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功能状态评分有181例为0分(69.6%),79例为1分(30.4%)。手术前肿瘤的平均长度25.50 mm。肿瘤部位分布较平均,右上叶(32.7%)占比最多。手术前的临床分期如下3例(1.2%)CR;54例(20.8%)为Ⅰ期;36例(13.8%)为Ⅱ期;153例(58.8%)为ⅢA期(T1~2N2、T3N1、T4N0~1),14例(5.4%)为ⅢB期[T3~4N2M0(单N2站)]。肺叶切除术是肺切除的主要方法(207例,79.6%),40例(15.4%)行肺袖式切除术,13例(5.0%)进行了全肺切除术。新辅助免疫+化疗112例(43.1%),靶向治疗82例(31.5%),化疗54例(20.8%),靶向+化疗6例(2.3%),免疫治疗3例(1.2%),免疫+靶向治疗2例(0.8%),免疫+靶向+化疗1例(0.4%)。173例(66.5%)患者未获得主要病理缓解(non-major pathologic response,NMPR),87例(33.5%)患者实现MPR,41例患者实现pCR(15.8%)。所有患者实现了根治性切除(R0)。根据术前规划的手术路径,分为VATS组(192例)和开胸组(68例),由于术中有8例VATS中转开胸患者,最终开胸组76例和VATS组184例,中转率为4.16%(8/192)。由于两组在性别、吸烟史、肿瘤直径、术前N分期、术前TNM分期、肺切除方式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些混杂因素可能影响围手术期结果,因此对两组进行了倾向性评分匹配。匹配后开胸组68例、VATS组113例,两组在基线期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与表2。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2.2 手术及病理结果
VATS组与开胸组经倾向性匹配后发现,VATS组手术时间更短(146 min vs.165 min,P=0.006)、术中失血量更少(50 mL vs.100 mL,P<0.001)、术中输血率更低(0% vs.7.4%,P=0.003)。两组在淋巴结清扫方面的表现比较类似,无论是淋巴结清扫站数、切除的淋巴结数量,还是采集到的阳性淋巴结数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样两组在胸膜累积、淋巴或血管累及上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两组术后的病理T分期、N分期和TNM分期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术后并发症
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开胸术组和VATS组在术后并发症(漏气、脓胸、肺栓塞、支气管胸膜瘘)、术后30 d再入院、术后30 d再手术、术后30 d死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开胸组和VATS组各有1例患者术后30 d再手术,原因都是肺袖式切除术后并发支气管胸膜瘘和脓胸,而VATS组再手术患者,在第二次手术后1 d因心力衰竭而死亡。但VATS组术后1、2、3 d引流量(250 mL vs.350 mL,P=0.011;180 mL vs.250 mL,P=0.002;150 mL vs.235 mL,P<0.001)更少、术后引流时间(9.34 d vs.13.84 d,P<0.001)和术后住院时间(6.19 d vs.7.94 d,P=0.006)更短。根据外科医生经验来看,新辅助治疗后手术患者可能容易出现如支气管胸膜瘘、吻合口瘘等并发症,为了减少并发症,部分患者带管出院;见表4。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2.4 免疫联合化疗亚组分析
我们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的数据中,提取免疫联合化疗患者的临床资料,进一步分析开胸组和VATS组在免疫联合化疗下的围手术期疗效差异。亚组分析显示,与整体新辅助治疗相仿。在手术时间、失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量和术后引流时间方面,VATS更具优势。两组淋巴结清扫方面、术后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同样,对倾向性评分匹配后的靶向、化疗亚组围手术期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7~8。化疗亚组结果与整体新辅助治疗类似,在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量方面,VATS更具优势(P<0.05)。而在靶向治疗亚组中,VATS手术时间更短(P<0.05),虽然在失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量和术后引流时间方面,VATS有表现更好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3 讨论
开胸手术和VATS是最常用的手术方式,特别是自从VATS被纳入胸外科手术以来,VATS在良性和恶性疾病中应用越来越普遍。VATS彻底改变了胸外科领域,现在是早期肺癌手术的首选路径。近年来新辅助疗法越来越多地用于NSCLC患者,新辅助治疗后最佳手术路径的选择存在争议。
以前VATS为新辅助化疗后患者的相对禁忌证。这是由于化疗可能导致肺部和肺门结构发现炎性改变,导致粘连形成,让VATS无法轻松有效地清扫纵隔淋巴结[18]。Kamel等[19]收集114例新辅助化疗后行肺叶切除术的患者资料,对比VATS组和开胸组围手术期的安全性(VATS 40例;开胸74例)。有5例因粘连中转开胸,中转率11%。结果发现,两组淋巴结清扫方面、R0切除率类似;但VATS在术中出血、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方面有更好的获益。该研究表明,新辅助化疗会对肺部解剖结构产生影响,造成手术难度的增加,但VATS仍然可以很好完成手术。
近年来,临床试验[20-22]报道新辅助靶向治疗带给部分驱动基因阳性患者ORR获益,然而新辅助靶向对手术的影响缺乏大规模报道。例如,NEOS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单臂、Ⅱ期研究,旨在评估新辅助奥希替尼在可切除肺腺癌中的疗效和安全性[20]。结果显示其客观缓解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为71.1%,他们认为大部分患者肿瘤明显缩小,相应降低了手术切除难度,提高了R0切除率。但手术难度不仅与肿瘤大小有关,更受到解剖结构影响。NEOS中50%行开胸手术,50%行微创手术,但并未做手术路径的亚组分析和报道术中细节,所以不清楚新辅助靶向治疗对解剖结构的影响。同样,NCT01833572[21]、NCT04201756[22]分别报道了吉非替尼与阿法替尼带来了ORR获益(51.6% vs. 70.2%),但都未描述对解剖结构的影响。有个案[23]报道,新辅助靶向+化疗相比新辅助靶向治疗,术中粘连更严重,化疗可能比靶向治疗更易增加手术难度。以及本中心手术医生大多认为新辅助靶向后病灶和淋巴结容易出现固缩、纤维化,手术难度增加,但没有进行相关统计分析,难以说明新辅助靶向治疗会导致手术难度增加。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也不能说明新辅助靶向治疗是否影响肺部解剖结构。但新辅助靶向治疗亚组分析表明,相比于开胸,VATS具有更短的手术时间,虽然在失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量和术后引流时间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这些方面的中位数都比开胸组的更有利一些,VATS在新辅助靶向治疗后应用是安全可行的。
自从ICIs问世以来,免疫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了曙光,越来越多的患者从中获益。然而免疫治疗存在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风险,导致局部炎症,使胸膜和肺组织发生致密粘连,甚至纤维化[6]。并且免疫治疗常常联合化疗,更容易产生粘连等手术风险。Bott等[6]报道新辅助免疫治疗后半数以上的微创转为开胸手术(7/13,54%),原因是肺门炎症和纤维化。王峥等[24]报道了相比于未治疗组,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组行肺袖式切除术的手术难度明显增加,主要原因是血管与支气管之间粘连紧密,但他们纳入的7例新辅助治疗患者都行VATS肺袖式切除术,且无中转开胸,这与他们手术医生都是高年资医生有关。表明VATS即使面对难度上升的复杂手术,仍然可以顺利进行。
总体来说,新辅助治疗会增加胸腔粘连、水肿和纤维化的风险,这可能会增加手术的复杂性和中转开胸的机率,尤其是对已经有明显治疗反应的患者[6, 19],但是在细致对待下VATS仍然可以较好地完成手术。本研究中有8例患者中转开胸手术,中转率为4.16%,中转率与既往研究类似[25]。其中有5例患者因粘连而中转,3例因术中出血而中转。靶向、化疗和免疫联合化疗各自的中转开胸率也接近(表3),未发现某种新辅助治疗会导致中转开胸率上升。本研究无法证实新辅助治疗与中转增加有关联,但从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和术中输血来看,可以肯定新辅助治疗后行VATS手术的优势以及安全性,
除此以外,淋巴结清扫也是影响着手术路径的选择。淋巴结清扫及采样是外科手术的必要组成部分,对N分期的确定和后续的治疗有着指导作用。根据O’Donnell等[26]的研究,术前新辅助治疗可导致严重粘连或融合淋巴结的形成,这些淋巴结会在手术中卡在血管分叉处,使肿瘤和淋巴结的分离和切除更具挑战性。由于肺和淋巴结切除术的难度和复杂性增加,为了确保安全性和更好的视野,一些外科医生更多选择开胸手术,而另一部分认为VATS同样能彻底清扫淋巴。Toker等[27]比较了淋巴结清扫术在开胸、VATS中的有效性,其发现VATS和开胸手术在淋巴结采集方面没有差异。而Zhang等[14]发现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VATS组总淋巴结和N2淋巴结的平均数量均低于开胸手术组。本研究中在清扫的淋巴结组数、淋巴结个数上,VATS组表现不亚于开胸组,VATS同样有助于获得准确的分期和良好的预后。手术路径的选择也与手术医生的习惯有关,相信随着外科医生新辅助治疗VATS手术经验的积累,更能发挥VATS的优势。
众多论文报道[7-10],与接受开胸手术相比,VATS手术后的并发症相当或更少。在新辅助治疗后这个前提下,本研究发现两组并发症(漏气、脓胸、肺栓塞、支气管胸膜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术后引流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上,VATS组表现更具优势。
本研究收集了新辅助治疗后行手术切除的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是目前国内报道关于NSCLC新辅助治疗后手术路径选择的最大规模的回顾性研究,并且比较了各种新辅助治疗后开胸与VATS手术的围手术期结果的差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VATS在各种新辅助治疗后应用安全可行,有着和开胸手术同样的R0切除率和淋巴结清扫能力,并且能够减少术中出血和术后引流、缩短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帮助患者更好地康复。因此,我们推荐VATS作为新辅助治疗后手术的首选,但需要做好充分术前评估,特别是面对有强烈新辅助治疗反应的患者,并且手术中要随时做好开胸的准备。
然而本研究是回顾性分析,难以避免出现偏倚。比如,部分困难手术在术前已选择开胸的方式,造成开胸组偏向大型的、复杂的手术,基线期资料显示开胸组有占比更高的肺袖式切除术与肺全切术。为了减少偏倚,我们进行倾向性匹配。此外,本研究因随访时间不足,缺少对比分析两种手术的远期预后情况。期待更多的前瞻性临床对照试验进一步探讨新辅助治疗后VATS的应用,为患者选择最佳的治疗方式。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卿阳负责数据整理及统计分析,论文撰写和修改;滕美新、姚王超负责论文筛选及收集数据;章靖、张鹏负责论文设计与审阅。
2023年美国癌症协会统计显示,肺癌现为全世界发病率第2、死亡率第1的恶性肿瘤,其中约85%的肺癌病理类型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1]。依据分期来行手术和辅助治疗是NSCLC的主要治疗方案,早期NSCLC患者通过手术切除后10年生存率极高,但大多数患者确诊NSCLC已为局部晚期,预后较差。近些年,新辅助治疗已被证实能够显著改善局部晚期NSCLC患者的总体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OS)及无复发生存率(recurrence-free survival,RFS)[2-5]。
而随着新辅助治疗在临床实践中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关于新辅助治疗后手术路径的争论也越来越多。新辅助治疗,特别是免疫治疗诱发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irAE)可能导致局部炎症,使胸膜和肺组织发生致密粘连,甚至纤维化[6]。这可能会增加手术视野的复杂性,因此手术路径选择至关重要。众所周知,在早期NSCLC的切除术中,电视胸腔镜辅助手术(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VATS)优于开胸手术,具有并发症少、疼痛轻、恢复快和长期生存率相当的优点[7-10];最近的研究[11-15]表明,NSCLC患者在新辅助化疗或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接受VATS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疗效。但这些报道基本为小样本,且多为新辅助化疗而关于其他新辅助治疗的报道较少,仍缺少NSCLC患者接受各种新辅助治疗后,VATS和开胸手术的对比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回顾性收集术前进行过新辅助治疗的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对NSCLC患者在接受新辅助治疗后手术的围手术期结果进行了初步探索,为NSCLC精准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本研究回顾性收集本院2020年6月—2022年5月NSCLC患者新辅助治疗后行VATS和开胸手术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术前行新辅助治疗(单药或联合用药)包括化疗、免疫疗法、靶向疗法。排除标准:(1)临床或影像学信息不完整;(2)既往有肺部手术史;(3)复发性NSCLC;(4)N3或远处转移;(5)术前放疗。
1.2 新辅助治疗及评价
所有纳入患者均行2~6周期新辅助治疗,其中化疗药物使用PP方案(培美曲塞+铂类)、TP方案(紫杉醇类+铂类)或者GP方案(吉西他滨+铂类)。免疫治疗药物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ICI),主要与化疗联合使用。靶向药物则根据患者驱动基因选择。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是指影像学上所有肿瘤靶病灶消失,无新病灶出现,且肿瘤标志物正常,至少维持4周。病理反应由上海市肺科医院病理科的专业人员进行评估。主要病理缓解(major pathological response,MPR)定义为:在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的病理评估中,残留肿瘤细胞≤10%[16]。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pCR)定义为:在切除的肿瘤或切除的淋巴结中无证据表明有肿瘤细胞存活。NSCLC新辅助治疗后病理分期采用美国癌症联合会第8版TNM分期系统,T分期中肿瘤大小调整为残存肿瘤的大小。N分期需要根据淋巴结内有无肿瘤细胞归入相应N分期。
1.3 手术治疗
经外科医师在内的多学科团队进行讨论,在新辅助治疗恢复后,将实施切除术。根据手术方法,患者被分为两组:VATS组:接受单孔或多孔胸腔镜手术患者;开胸手术组:接受传统开胸手术患者。所有患者均行根治性手术,切除肿瘤和阴性切缘(支气管、动脉、静脉、支气管周围、肿瘤附近组织),并清扫纵膈淋巴结。镜下切缘阴性为R0,镜下切缘阳性R1,肉眼可见肿瘤残余为R2[17]。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数据统计分析采用R软件(4.3.2版),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类变量以频数和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四格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呈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则采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并采用两组比较的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分析。倾向性评分匹配使用matchit函数,卡钳值为0.2。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则采用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并采用两组比较的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分析。倾向性评分匹配使用matchit函数,卡钳值为0.2。
1.5 伦理审查
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规定,并通过上海市肺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K23-004;批准日期:2022年2月22日)。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特征
共纳入260例,男性占队列的71.9%,女性占队列28.1%。全部患者平均年龄(60.08±8.97)岁。114例患者(43.8%)确诊前未戒烟。主要组织学类型为腺癌(178例,68.5%)和鳞癌(70例,26.9%)。ASA评分都≤3分,大多为2分(89.6%)。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功能状态评分有181例为0分(69.6%),79例为1分(30.4%)。手术前肿瘤的平均长度25.50 mm。肿瘤部位分布较平均,右上叶(32.7%)占比最多。手术前的临床分期如下3例(1.2%)CR;54例(20.8%)为Ⅰ期;36例(13.8%)为Ⅱ期;153例(58.8%)为ⅢA期(T1~2N2、T3N1、T4N0~1),14例(5.4%)为ⅢB期[T3~4N2M0(单N2站)]。肺叶切除术是肺切除的主要方法(207例,79.6%),40例(15.4%)行肺袖式切除术,13例(5.0%)进行了全肺切除术。新辅助免疫+化疗112例(43.1%),靶向治疗82例(31.5%),化疗54例(20.8%),靶向+化疗6例(2.3%),免疫治疗3例(1.2%),免疫+靶向治疗2例(0.8%),免疫+靶向+化疗1例(0.4%)。173例(66.5%)患者未获得主要病理缓解(non-major pathologic response,NMPR),87例(33.5%)患者实现MPR,41例患者实现pCR(15.8%)。所有患者实现了根治性切除(R0)。根据术前规划的手术路径,分为VATS组(192例)和开胸组(68例),由于术中有8例VATS中转开胸患者,最终开胸组76例和VATS组184例,中转率为4.16%(8/192)。由于两组在性别、吸烟史、肿瘤直径、术前N分期、术前TNM分期、肺切除方式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些混杂因素可能影响围手术期结果,因此对两组进行了倾向性评分匹配。匹配后开胸组68例、VATS组113例,两组在基线期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与表2。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2.2 手术及病理结果
VATS组与开胸组经倾向性匹配后发现,VATS组手术时间更短(146 min vs.165 min,P=0.006)、术中失血量更少(50 mL vs.100 mL,P<0.001)、术中输血率更低(0% vs.7.4%,P=0.003)。两组在淋巴结清扫方面的表现比较类似,无论是淋巴结清扫站数、切除的淋巴结数量,还是采集到的阳性淋巴结数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同样两组在胸膜累积、淋巴或血管累及上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两组术后的病理T分期、N分期和TNM分期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 术后并发症
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开胸术组和VATS组在术后并发症(漏气、脓胸、肺栓塞、支气管胸膜瘘)、术后30 d再入院、术后30 d再手术、术后30 d死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开胸组和VATS组各有1例患者术后30 d再手术,原因都是肺袖式切除术后并发支气管胸膜瘘和脓胸,而VATS组再手术患者,在第二次手术后1 d因心力衰竭而死亡。但VATS组术后1、2、3 d引流量(250 mL vs.350 mL,P=0.011;180 mL vs.250 mL,P=0.002;150 mL vs.235 mL,P<0.001)更少、术后引流时间(9.34 d vs.13.84 d,P<0.001)和术后住院时间(6.19 d vs.7.94 d,P=0.006)更短。根据外科医生经验来看,新辅助治疗后手术患者可能容易出现如支气管胸膜瘘、吻合口瘘等并发症,为了减少并发症,部分患者带管出院;见表4。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2.4 免疫联合化疗亚组分析
我们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的数据中,提取免疫联合化疗患者的临床资料,进一步分析开胸组和VATS组在免疫联合化疗下的围手术期疗效差异。亚组分析显示,与整体新辅助治疗相仿。在手术时间、失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量和术后引流时间方面,VATS更具优势。两组淋巴结清扫方面、术后并发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同样,对倾向性评分匹配后的靶向、化疗亚组围手术期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7~8。化疗亚组结果与整体新辅助治疗类似,在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量方面,VATS更具优势(P<0.05)。而在靶向治疗亚组中,VATS手术时间更短(P<0.05),虽然在失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量和术后引流时间方面,VATS有表现更好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3 讨论
开胸手术和VATS是最常用的手术方式,特别是自从VATS被纳入胸外科手术以来,VATS在良性和恶性疾病中应用越来越普遍。VATS彻底改变了胸外科领域,现在是早期肺癌手术的首选路径。近年来新辅助疗法越来越多地用于NSCLC患者,新辅助治疗后最佳手术路径的选择存在争议。
以前VATS为新辅助化疗后患者的相对禁忌证。这是由于化疗可能导致肺部和肺门结构发现炎性改变,导致粘连形成,让VATS无法轻松有效地清扫纵隔淋巴结[18]。Kamel等[19]收集114例新辅助化疗后行肺叶切除术的患者资料,对比VATS组和开胸组围手术期的安全性(VATS 40例;开胸74例)。有5例因粘连中转开胸,中转率11%。结果发现,两组淋巴结清扫方面、R0切除率类似;但VATS在术中出血、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方面有更好的获益。该研究表明,新辅助化疗会对肺部解剖结构产生影响,造成手术难度的增加,但VATS仍然可以很好完成手术。
近年来,临床试验[20-22]报道新辅助靶向治疗带给部分驱动基因阳性患者ORR获益,然而新辅助靶向对手术的影响缺乏大规模报道。例如,NEOS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单臂、Ⅱ期研究,旨在评估新辅助奥希替尼在可切除肺腺癌中的疗效和安全性[20]。结果显示其客观缓解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为71.1%,他们认为大部分患者肿瘤明显缩小,相应降低了手术切除难度,提高了R0切除率。但手术难度不仅与肿瘤大小有关,更受到解剖结构影响。NEOS中50%行开胸手术,50%行微创手术,但并未做手术路径的亚组分析和报道术中细节,所以不清楚新辅助靶向治疗对解剖结构的影响。同样,NCT01833572[21]、NCT04201756[22]分别报道了吉非替尼与阿法替尼带来了ORR获益(51.6% vs. 70.2%),但都未描述对解剖结构的影响。有个案[23]报道,新辅助靶向+化疗相比新辅助靶向治疗,术中粘连更严重,化疗可能比靶向治疗更易增加手术难度。以及本中心手术医生大多认为新辅助靶向后病灶和淋巴结容易出现固缩、纤维化,手术难度增加,但没有进行相关统计分析,难以说明新辅助靶向治疗会导致手术难度增加。遗憾的是,我们的研究也不能说明新辅助靶向治疗是否影响肺部解剖结构。但新辅助靶向治疗亚组分析表明,相比于开胸,VATS具有更短的手术时间,虽然在失血量、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引流量和术后引流时间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这些方面的中位数都比开胸组的更有利一些,VATS在新辅助靶向治疗后应用是安全可行的。
自从ICIs问世以来,免疫治疗为肺癌患者带来了曙光,越来越多的患者从中获益。然而免疫治疗存在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风险,导致局部炎症,使胸膜和肺组织发生致密粘连,甚至纤维化[6]。并且免疫治疗常常联合化疗,更容易产生粘连等手术风险。Bott等[6]报道新辅助免疫治疗后半数以上的微创转为开胸手术(7/13,54%),原因是肺门炎症和纤维化。王峥等[24]报道了相比于未治疗组,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组行肺袖式切除术的手术难度明显增加,主要原因是血管与支气管之间粘连紧密,但他们纳入的7例新辅助治疗患者都行VATS肺袖式切除术,且无中转开胸,这与他们手术医生都是高年资医生有关。表明VATS即使面对难度上升的复杂手术,仍然可以顺利进行。
总体来说,新辅助治疗会增加胸腔粘连、水肿和纤维化的风险,这可能会增加手术的复杂性和中转开胸的机率,尤其是对已经有明显治疗反应的患者[6, 19],但是在细致对待下VATS仍然可以较好地完成手术。本研究中有8例患者中转开胸手术,中转率为4.16%,中转率与既往研究类似[25]。其中有5例患者因粘连而中转,3例因术中出血而中转。靶向、化疗和免疫联合化疗各自的中转开胸率也接近(表3),未发现某种新辅助治疗会导致中转开胸率上升。本研究无法证实新辅助治疗与中转增加有关联,但从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和术中输血来看,可以肯定新辅助治疗后行VATS手术的优势以及安全性,
除此以外,淋巴结清扫也是影响着手术路径的选择。淋巴结清扫及采样是外科手术的必要组成部分,对N分期的确定和后续的治疗有着指导作用。根据O’Donnell等[26]的研究,术前新辅助治疗可导致严重粘连或融合淋巴结的形成,这些淋巴结会在手术中卡在血管分叉处,使肿瘤和淋巴结的分离和切除更具挑战性。由于肺和淋巴结切除术的难度和复杂性增加,为了确保安全性和更好的视野,一些外科医生更多选择开胸手术,而另一部分认为VATS同样能彻底清扫淋巴。Toker等[27]比较了淋巴结清扫术在开胸、VATS中的有效性,其发现VATS和开胸手术在淋巴结采集方面没有差异。而Zhang等[14]发现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后,VATS组总淋巴结和N2淋巴结的平均数量均低于开胸手术组。本研究中在清扫的淋巴结组数、淋巴结个数上,VATS组表现不亚于开胸组,VATS同样有助于获得准确的分期和良好的预后。手术路径的选择也与手术医生的习惯有关,相信随着外科医生新辅助治疗VATS手术经验的积累,更能发挥VATS的优势。
众多论文报道[7-10],与接受开胸手术相比,VATS手术后的并发症相当或更少。在新辅助治疗后这个前提下,本研究发现两组并发症(漏气、脓胸、肺栓塞、支气管胸膜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出血量、术后引流量、术后引流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上,VATS组表现更具优势。
本研究收集了新辅助治疗后行手术切除的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是目前国内报道关于NSCLC新辅助治疗后手术路径选择的最大规模的回顾性研究,并且比较了各种新辅助治疗后开胸与VATS手术的围手术期结果的差异,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VATS在各种新辅助治疗后应用安全可行,有着和开胸手术同样的R0切除率和淋巴结清扫能力,并且能够减少术中出血和术后引流、缩短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帮助患者更好地康复。因此,我们推荐VATS作为新辅助治疗后手术的首选,但需要做好充分术前评估,特别是面对有强烈新辅助治疗反应的患者,并且手术中要随时做好开胸的准备。
然而本研究是回顾性分析,难以避免出现偏倚。比如,部分困难手术在术前已选择开胸的方式,造成开胸组偏向大型的、复杂的手术,基线期资料显示开胸组有占比更高的肺袖式切除术与肺全切术。为了减少偏倚,我们进行倾向性匹配。此外,本研究因随访时间不足,缺少对比分析两种手术的远期预后情况。期待更多的前瞻性临床对照试验进一步探讨新辅助治疗后VATS的应用,为患者选择最佳的治疗方式。
 /M(P25,P75)/例数(%)]
/M(P25,P75)/例数(%)]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卿阳负责数据整理及统计分析,论文撰写和修改;滕美新、姚王超负责论文筛选及收集数据;章靖、张鹏负责论文设计与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