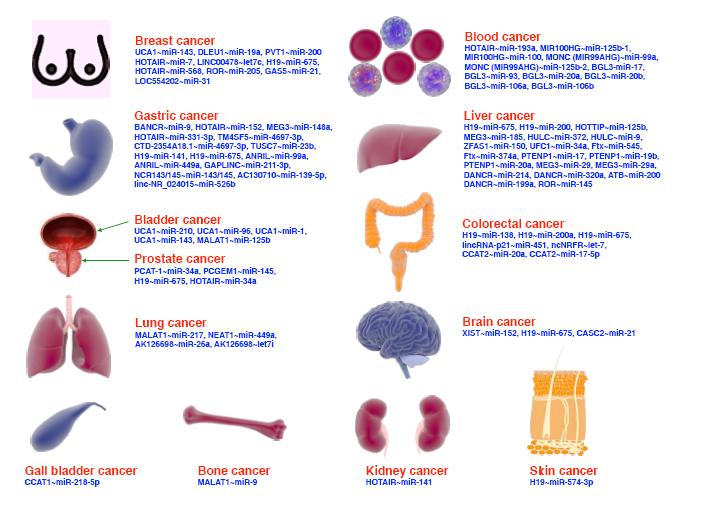本文报道了3例在东部战区总医院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体部立体定向放疗的Ⅲ/N2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结局,其中男2例、女1例,平均年龄65.7岁。患者在接受体部立体定向放疗1周后接受了2剂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抑制剂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并计划在第2次给药后4~6周进行手术。1例患者达到完全病理学缓解,1例患者达到主要病理学缓解,1例患者残留20%肿瘤,未达到主要病理学缓解。特瑞普利单抗联合体部立体定向放疗作为新辅助治疗副作用少,且治疗没有造成手术延误。
引用本文: 王振, 顾浩宇, 罗静, 朱熙煦, 宋勇, 申翼, 强勇. 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体部立体定向放疗Ⅲ/N2期非小细胞肺癌三例.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3, 30(8): 1210-1216. doi: 10.7507/1007-4848.202210022 复制
Ⅲ期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5年生存率为13%~36%,且大多数患者有术后肿瘤复发[1]。在接受包括手术在内的多模式治疗的Ⅲ期NSCLC患者中,很少有报告>5年长期生存结果的患者。围手术期以铂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的生存率仅比单纯手术高5%,且发生三级或更高毒副作用的概率>60%[2]。同时,在新辅助化疗中联合放疗并不能提高Ⅲ/N2期NSCLC患者无事件生存率或总生存率[3]。因此,新辅助治疗方案一直是临床医生研究的重点。
目前,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抑制剂为肺癌患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选择。对于Ⅲ期不能切除的NSCLC且放化疗后无进展的患者,这些抗体可以激活抗肿瘤免疫,导致肿瘤缩小,提高存活率[4-5]。在新辅助治疗方面,Forde等[6]在纳入22例早期NSCLC患者的研究中首次报道了新辅助纳武单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术后主要病理学缓解(major pathologic response,MPR)率为45%,高于传统新辅助化疗(20%~30%)。
本研究报道3例Ⅲ期NSCLC患者在东部战区总医院接受新辅助免疫疗法联合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和手术治疗的结果。患者在第1周接受SBRT,然后每3周静脉注射两剂特瑞普利单抗(PD-1抑制剂,240 mg),计划在第2次注射后大约4~6周进行手术,后特瑞普利单抗维持性治疗1年。主要终点是安全性和可行性,次要终点是病理学缓解率。
临床资料 患者1,男,68岁,主诉咳嗽、咳血痰,2020年6月于我院接受治疗。有吸烟史(50包年),无明显其他病史。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显示原发灶为低分化腺癌(图1a)。免疫组织化学(组化)结果显示:TTF-1表达(3+),NapsinA阳性(1+),P40阴性,Ki-67指数20%,80%的癌细胞有PD-1配体(PD-1 ligand,PD-L1)表达(图1b),未见ALK和ROS-1表达。
 图1
患者1的病理学检测
图1
患者1的病理学检测
a:治疗前肿瘤活检的苏木精-伊红染色显示浸润性腺癌,低分化,腺泡实性亚型;b: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高表达,肿瘤细胞阳性比例评分约80%;c~d:分别为左侧上肺病变区和肺门淋巴结术后病理,广泛纤维化坏死,无存活癌细胞残留
下一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没有发现任何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靶向突变和高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18.46 Muts/Mb)。根据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结合CT(fluorodeoxyglucose-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FDG-PET/CT)(图2a)和增强脑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TNM分期(第8版)为cT3cN2bcM0期,与cⅢB分期一致。T3分期是基于肿瘤大小(6.7 cm),N2分期是基于4L和5区纵隔淋巴结的高代谢增大,但没有细胞和组织学证实。
 图2
患者1的放射学检查
图2
患者1的放射学检查
a: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基线显示左上肺叶肺门附近有一肿块,大小约6.7 cm×4.2 cm,最大标准摄取值为17.7;b:治疗前胸部CT扫描;c:治疗后胸部CT扫描,左上肺病变缩小,放射学评估为肿瘤部分缓解
患者在第1周接受SBRT(50 Gy/5f),随后接受两周期特瑞普利单抗(240 mg,每3周1次)。剂量当量采用线性二次模型估计,并假设a/b=10 Gy for the tumor。生物等效剂量为100 Gy。两周期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后CT扫描,疗效评估为肿瘤部分缓解,左肺肿块显著减小(图2b~c)。此外,完善颅脑MRI排除脑转移。于2020年9月,即结束特瑞普利单抗治疗4周后,行开胸左上肺癌根治切除、左下肺动脉袖状成形、淋巴结清扫术(分别清扫4L、5、6、7、9、10、11、12、13、14组淋巴结),切缘完整,未见癌细胞累及。
切除的肺和淋巴结组织学分析显示,除肺坏死和纤维化外,并未发现残留的肿瘤细胞(图1c~d)。根据病理学TNM分期(第8版)为ypT0ypN0期(R0切除)。术后继续特瑞普利单抗辅助治疗。2021年3月,即手术切除6个月后,患者仍处于完全缓解状态,但出现了2级放射性肺纤维化和2级免疫相关瘙痒。
患者2,男,63岁,主诉左侧胸痛,2020年6月于我院接受治疗。有吸烟史(40包年),无明显其他病史。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术活检显示原发灶为低分化腺癌(图3a)。免疫组化显示:TTF-1表达(2+),NapsinA阳性(2+),CKpan阳性(3+),Ki-67指数30%,PD-L1阴性(图3b),少量CD4+T细胞和CD8+T细胞浸润(图3c~d)。
 图3
患者2的病理学检测
图3
患者2的病理学检测
a:治疗前肿瘤活检病理显示低分化腺癌;b: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阴性(肿瘤细胞阳性比例评分0);c:少量CD4+T细胞浸润(CD4+T细胞在热点区约占5%);d:少量CD8+T细胞浸润(CD8+T细胞在热点区约占10%);e:术后病理显示低分化浸润性腺癌;f:术后免疫组化显示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阴性(肿瘤细胞阳性比例评分1%);g~h:分别为术后CD4+T细胞和CD8+T细胞浸润,分别占热点区约10%和15%,此外还可见大片的坏死斑块、组织细胞反应和胆固醇晶体沉积
基因检测提示:EGFR、ROS1、HER2、NRAS、BRAF、PIK3CA、KRAS和ALK试验均为阴性。基于增强CT和脑MRI的TNM分期(第8版)为cT3cN2a2cM0期,与cⅢB疾病分期一致。CT显示左下叶有2个相邻的病灶,其直径分别为4.0 cm和2.7 cm。隆突下淋巴结短径1.0 cm。
该患者还接受了左下肺病变的SBRT(50 Gy/5f)和两周期的特瑞普利单抗(240 mg,每3周1次)治疗。两周期的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后,CT扫描显示轻微反应:左下肺病变缩小29%(图4)。
 图4
患者2的放射学检查
图4
患者2的放射学检查
a~b:新辅助治疗前胸部CT显示左肺下叶两个相邻病变;c~d:新辅助治疗后胸部CT显示病变收缩29%
术前完善颅脑MRI检查排除脑转移。于2020年9月即第2次给药后4周,行胸腔镜下左下肺叶切除术和淋巴结清扫术(清扫第5~6,7~9,10~14组淋巴结),切缘完整,未见癌细胞累及。
术后肺和淋巴结标本中可见浸润性腺癌,并伴有大量坏死细胞(图3e)。PD-L1的表达水平也增加(图3f)。对所有病变的综合评价显示肿瘤残留占20%。CD4+T细胞和CD8+T细胞的数量明显增加(图3g~h)。因此,病理TNM分期为ypT3ypN2期(R0切除)。术后继续特瑞普利单抗维持治疗。手术切除5个月后,患者共计接受6个周期的免疫维持治疗,并且没有观察到不良反应。
患者3,女,66岁,2020年5月于我院接受治疗。该患者有脑梗死、高血压和糖尿病,并长期口服抗凝药物,无吸烟史。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术活检的组织学分析显示原发灶为肺腺癌(图5a)。免疫组化显示:TTF-1表达(+),NapsinA阴性(−),Ki-67指数10%,PD-L1在10%的癌细胞中表达。NGS未发现任何TKI靶向突变,酪氨酸激酶受体2阳性。根据FDG-PET/CT和增强MRI,TNM分期为cT2acN2a2cM0期,与cⅢA疾病分期一致。左上叶病变大小为32 mm,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max)为9.35。肺门和纵隔6区(腹主动脉弓旁)转移淋巴结的SUVmax分别为8.1和8.8(图5b~c)。
 图5
患者3的病理学和放射学检查
图5
患者3的病理学和放射学检查
a:治疗前肿瘤活检的苏木精-伊红染色显示浸润性腺癌;b:左上肺叶后段可见圆形肿块,大小约32 mm×27 mm,最大标准摄取值为9.35;c:左肺门、纵隔6区可见多发肿大淋巴结,最大标准摄取值分别为8.1和8.8;d:治疗后肺门淋巴结无残留活癌细胞
由于急性脑梗死,手术无法进行。因此,患者选择先接受新辅助治疗,然后根据情况进行手术。左下肺病灶采用SBRT(50 Gy/5f)联合两周期的特瑞普利单抗(240 mg,每3周1次)治疗。两周期的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后CT扫描显示轻微反应:左肺肿块减少20%。脑部MRI排除脑转移瘤。然而脑梗死再次发生,所以首先对脑梗死进行短暂治疗后,特瑞普利单抗治疗于2020年9月1日和24日实施。
患者于2020年12月1日行开胸左上肺叶切除和淋巴结清扫术(清扫5~6,7,9,10,11,12组淋巴结),切缘完整,未见癌细胞累及。术后病理显示病变内轻度腺体发育不良,浸润性腺癌。可见间质增生、变性、坏死,并有大量慢性炎症细胞和组织细胞浸润。纵隔和肺门淋巴结均为阴性(图5d)。综合评价,残留肿瘤细胞占1%,达到MPR。因此,病理TNM分期(第8版)为ypT3ypN0期(R0切除)。术后出现胸痛(数字疼痛评分5分),并在术后1个月逐渐好转。目前患者正在接受4个周期的免疫维持治疗,未观察到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
本研究经东部战区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2019NZKY-025-01),患者和参与者都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书。
讨论 本研究3例患者中,1例完全病理学缓解,1例MPR,1例残留20%肿瘤。没有因毒副作用而延迟手术,也没有严重围手术期并发症和3级及以上肺炎发生。我们的结果与其他关于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研究[6-7]相似。放射学和病理学上的缓解是不同的,持续性肿瘤肿块并不代表残留的活动性癌症。
在化疗时代,新辅助化疗联合放疗并不能改善Ⅲ/N2期NSCLC的MPR率、无事件率和总体生存率,可能的原因是常规放疗剂量不足、手术间期时间长[3]。SBRT是一种精确的放疗模型,可以显著增加辐射剂量,同时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在治疗肺癌和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方面疗效良好且优于常规放疗[8-11]。新辅助SBRT被证实耐受性良好、安全,早期NSCLC在SBRT治疗后MPR率为60%[12]。但对于Ⅲ/N2期NSCLC,需要与更有效的系统治疗相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出现为NSCLC的治疗带来了新希望。与新辅助化疗相比,新辅助抗PD-1或抗PD-L1单药治疗早期NSCLC的MPR率更高[6,13-14]。放疗通过释放新抗原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上调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表达和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来增强免疫应答[15-18]。在Ⅰ~Ⅲ期NSCLC患者中进行的新辅助德瓦鲁(durvalumab)单抗联合或不联合SBRT的随机2期试验[19]结果显示,durvalumab单抗联合SBRT(8 Gy×3组分)与高MPR率有关(53.3% vs. 6.7%,P<0.0001)。与本研究的一个不同之处是,50 Gy/5次的照射剂量相当于100 Gy/次的照射剂量,远高于8 Gy/3次的照射剂量(43.2 Gy)。虽然没有发生3级以上毒性反应,但是否需要如此高的放射剂量值得商榷。
对于不能切除的局部晚期NSCLC,标准胸部照射范围包括肺部病灶和肿瘤相关引流淋巴结(draining lymph node,DLN)。与此相反,在我们的研究中,对肺部病灶进行了SBRT,DLN未受到照射。主要考虑因素如下:(1)DLN是树突状细胞激活抗原特异性CD8+T细胞的主要部位[20];(2)大剂量照射肺部病变和转移的淋巴结并不能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免疫系统的高剂量辐射与第三阶段NSCLC最终治疗后的肿瘤进展和死亡相关[21-22];(3)临床前研究[23]表明,DLN的照射通过改变趋化因子的表达和CD8+T细胞的转运来抑制适应性免疫反应,所以当SBRT与免疫治疗相结合时,把DLN的放射区域排除是值得考虑的;(4)场外效率由常规放疗的10%提高到SBRT联合免疫治疗的38%[24]。对肺部病变进行SBRT治疗,不仅降低了手术难度,而且减少了放疗对淋巴结的损伤。本研究的3例患者中,患者1和患者3在新辅助治疗前通过PET/CT检查证实有淋巴结转移。新辅助治疗后,术中采集淋巴结标本未发现癌细胞。上述结果表明,即使淋巴结转移没有接受放疗,也可以获得良好的控制,这可能是免疫治疗和SBRT引起的非局部性效应导致的。
与PD-L1阳性患者相比,SBRT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PD-L1阴性患者的生存预后改善更明显。Theelen等[25]的一项Ⅱ期临床研究中,对晚期NSCLC患者的单个肿瘤病变进行了SBRT,后采用派姆单抗治疗。亚组分析表明,PD-L1阴性肿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显著延长,这表明放疗可能改变PD-L1阴性肿瘤的微环境,从而促进派姆单抗的作用。本研究中,患者2在治疗前PD-L1阴性。术后标本与细针抽吸标本相比,CD4+T细胞和CD8+T细胞计数升高。虽然患者1的PD-L1表达为80%,但将术前穿刺活检和术后标本进行比较,CD4+T细胞和CD8+T细胞并没有增加。未来需进一步评估PD-L1表达对治疗前后CD4+T细胞和CD8+T细胞的影响。
尽管SBRT联合PD-1抑制剂临床疗效较好,但联合用药可能引起重叠损伤,导致致死性重组相关免疫反应发生率高于单药治疗[26]。本研究发现特瑞普利单抗联合SBRT作为新辅助治疗几乎无副作用,该治疗没有导致手术延迟。但本研究仅在3例患者中进行了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SBRT治疗,且随访期较短。由于数据有限,未来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证实该方案的安全性和长期有效性。目前,评估新辅助免疫疗法联合放疗的前瞻性研究(NCT03237377、NCT0290495、NCT03217071和NCT02904954)在进行中,结果尚待公布。本中心也注册了类似的研究(ChiCTR2000029277)。这些研究需要长期随访,以确定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放疗的安全性、长期疗效、照射范围和剂量。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王振、宋勇、申翼、强勇负责论文设计;王振、罗静、强勇负责数据整理与分析;王振、顾浩宇、罗静负责论文初稿撰写;朱熙煦、宋勇、申翼、强勇负责论文审阅和修改。
Ⅲ期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患者5年生存率为13%~36%,且大多数患者有术后肿瘤复发[1]。在接受包括手术在内的多模式治疗的Ⅲ期NSCLC患者中,很少有报告>5年长期生存结果的患者。围手术期以铂为基础的新辅助化疗的生存率仅比单纯手术高5%,且发生三级或更高毒副作用的概率>60%[2]。同时,在新辅助化疗中联合放疗并不能提高Ⅲ/N2期NSCLC患者无事件生存率或总生存率[3]。因此,新辅助治疗方案一直是临床医生研究的重点。
目前,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抑制剂为肺癌患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选择。对于Ⅲ期不能切除的NSCLC且放化疗后无进展的患者,这些抗体可以激活抗肿瘤免疫,导致肿瘤缩小,提高存活率[4-5]。在新辅助治疗方面,Forde等[6]在纳入22例早期NSCLC患者的研究中首次报道了新辅助纳武单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术后主要病理学缓解(major pathologic response,MPR)率为45%,高于传统新辅助化疗(20%~30%)。
本研究报道3例Ⅲ期NSCLC患者在东部战区总医院接受新辅助免疫疗法联合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SBRT)和手术治疗的结果。患者在第1周接受SBRT,然后每3周静脉注射两剂特瑞普利单抗(PD-1抑制剂,240 mg),计划在第2次注射后大约4~6周进行手术,后特瑞普利单抗维持性治疗1年。主要终点是安全性和可行性,次要终点是病理学缓解率。
临床资料 患者1,男,68岁,主诉咳嗽、咳血痰,2020年6月于我院接受治疗。有吸烟史(50包年),无明显其他病史。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活检显示原发灶为低分化腺癌(图1a)。免疫组织化学(组化)结果显示:TTF-1表达(3+),NapsinA阳性(1+),P40阴性,Ki-67指数20%,80%的癌细胞有PD-1配体(PD-1 ligand,PD-L1)表达(图1b),未见ALK和ROS-1表达。
 图1
患者1的病理学检测
图1
患者1的病理学检测
a:治疗前肿瘤活检的苏木精-伊红染色显示浸润性腺癌,低分化,腺泡实性亚型;b: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高表达,肿瘤细胞阳性比例评分约80%;c~d:分别为左侧上肺病变区和肺门淋巴结术后病理,广泛纤维化坏死,无存活癌细胞残留
下一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技术没有发现任何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靶向突变和高肿瘤突变负荷(tumor mutational burden,TMB,18.46 Muts/Mb)。根据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结合CT(fluorodeoxyglucose-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FDG-PET/CT)(图2a)和增强脑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TNM分期(第8版)为cT3cN2bcM0期,与cⅢB分期一致。T3分期是基于肿瘤大小(6.7 cm),N2分期是基于4L和5区纵隔淋巴结的高代谢增大,但没有细胞和组织学证实。
 图2
患者1的放射学检查
图2
患者1的放射学检查
a: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基线显示左上肺叶肺门附近有一肿块,大小约6.7 cm×4.2 cm,最大标准摄取值为17.7;b:治疗前胸部CT扫描;c:治疗后胸部CT扫描,左上肺病变缩小,放射学评估为肿瘤部分缓解
患者在第1周接受SBRT(50 Gy/5f),随后接受两周期特瑞普利单抗(240 mg,每3周1次)。剂量当量采用线性二次模型估计,并假设a/b=10 Gy for the tumor。生物等效剂量为100 Gy。两周期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后CT扫描,疗效评估为肿瘤部分缓解,左肺肿块显著减小(图2b~c)。此外,完善颅脑MRI排除脑转移。于2020年9月,即结束特瑞普利单抗治疗4周后,行开胸左上肺癌根治切除、左下肺动脉袖状成形、淋巴结清扫术(分别清扫4L、5、6、7、9、10、11、12、13、14组淋巴结),切缘完整,未见癌细胞累及。
切除的肺和淋巴结组织学分析显示,除肺坏死和纤维化外,并未发现残留的肿瘤细胞(图1c~d)。根据病理学TNM分期(第8版)为ypT0ypN0期(R0切除)。术后继续特瑞普利单抗辅助治疗。2021年3月,即手术切除6个月后,患者仍处于完全缓解状态,但出现了2级放射性肺纤维化和2级免疫相关瘙痒。
患者2,男,63岁,主诉左侧胸痛,2020年6月于我院接受治疗。有吸烟史(40包年),无明显其他病史。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术活检显示原发灶为低分化腺癌(图3a)。免疫组化显示:TTF-1表达(2+),NapsinA阳性(2+),CKpan阳性(3+),Ki-67指数30%,PD-L1阴性(图3b),少量CD4+T细胞和CD8+T细胞浸润(图3c~d)。
 图3
患者2的病理学检测
图3
患者2的病理学检测
a:治疗前肿瘤活检病理显示低分化腺癌;b: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阴性(肿瘤细胞阳性比例评分0);c:少量CD4+T细胞浸润(CD4+T细胞在热点区约占5%);d:少量CD8+T细胞浸润(CD8+T细胞在热点区约占10%);e:术后病理显示低分化浸润性腺癌;f:术后免疫组化显示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配体阴性(肿瘤细胞阳性比例评分1%);g~h:分别为术后CD4+T细胞和CD8+T细胞浸润,分别占热点区约10%和15%,此外还可见大片的坏死斑块、组织细胞反应和胆固醇晶体沉积
基因检测提示:EGFR、ROS1、HER2、NRAS、BRAF、PIK3CA、KRAS和ALK试验均为阴性。基于增强CT和脑MRI的TNM分期(第8版)为cT3cN2a2cM0期,与cⅢB疾病分期一致。CT显示左下叶有2个相邻的病灶,其直径分别为4.0 cm和2.7 cm。隆突下淋巴结短径1.0 cm。
该患者还接受了左下肺病变的SBRT(50 Gy/5f)和两周期的特瑞普利单抗(240 mg,每3周1次)治疗。两周期的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后,CT扫描显示轻微反应:左下肺病变缩小29%(图4)。
 图4
患者2的放射学检查
图4
患者2的放射学检查
a~b:新辅助治疗前胸部CT显示左肺下叶两个相邻病变;c~d:新辅助治疗后胸部CT显示病变收缩29%
术前完善颅脑MRI检查排除脑转移。于2020年9月即第2次给药后4周,行胸腔镜下左下肺叶切除术和淋巴结清扫术(清扫第5~6,7~9,10~14组淋巴结),切缘完整,未见癌细胞累及。
术后肺和淋巴结标本中可见浸润性腺癌,并伴有大量坏死细胞(图3e)。PD-L1的表达水平也增加(图3f)。对所有病变的综合评价显示肿瘤残留占20%。CD4+T细胞和CD8+T细胞的数量明显增加(图3g~h)。因此,病理TNM分期为ypT3ypN2期(R0切除)。术后继续特瑞普利单抗维持治疗。手术切除5个月后,患者共计接受6个周期的免疫维持治疗,并且没有观察到不良反应。
患者3,女,66岁,2020年5月于我院接受治疗。该患者有脑梗死、高血压和糖尿病,并长期口服抗凝药物,无吸烟史。CT引导下经皮肺穿刺术活检的组织学分析显示原发灶为肺腺癌(图5a)。免疫组化显示:TTF-1表达(+),NapsinA阴性(−),Ki-67指数10%,PD-L1在10%的癌细胞中表达。NGS未发现任何TKI靶向突变,酪氨酸激酶受体2阳性。根据FDG-PET/CT和增强MRI,TNM分期为cT2acN2a2cM0期,与cⅢA疾病分期一致。左上叶病变大小为32 mm,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max)为9.35。肺门和纵隔6区(腹主动脉弓旁)转移淋巴结的SUVmax分别为8.1和8.8(图5b~c)。
 图5
患者3的病理学和放射学检查
图5
患者3的病理学和放射学检查
a:治疗前肿瘤活检的苏木精-伊红染色显示浸润性腺癌;b:左上肺叶后段可见圆形肿块,大小约32 mm×27 mm,最大标准摄取值为9.35;c:左肺门、纵隔6区可见多发肿大淋巴结,最大标准摄取值分别为8.1和8.8;d:治疗后肺门淋巴结无残留活癌细胞
由于急性脑梗死,手术无法进行。因此,患者选择先接受新辅助治疗,然后根据情况进行手术。左下肺病灶采用SBRT(50 Gy/5f)联合两周期的特瑞普利单抗(240 mg,每3周1次)治疗。两周期的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后CT扫描显示轻微反应:左肺肿块减少20%。脑部MRI排除脑转移瘤。然而脑梗死再次发生,所以首先对脑梗死进行短暂治疗后,特瑞普利单抗治疗于2020年9月1日和24日实施。
患者于2020年12月1日行开胸左上肺叶切除和淋巴结清扫术(清扫5~6,7,9,10,11,12组淋巴结),切缘完整,未见癌细胞累及。术后病理显示病变内轻度腺体发育不良,浸润性腺癌。可见间质增生、变性、坏死,并有大量慢性炎症细胞和组织细胞浸润。纵隔和肺门淋巴结均为阴性(图5d)。综合评价,残留肿瘤细胞占1%,达到MPR。因此,病理TNM分期(第8版)为ypT3ypN0期(R0切除)。术后出现胸痛(数字疼痛评分5分),并在术后1个月逐渐好转。目前患者正在接受4个周期的免疫维持治疗,未观察到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
本研究经东部战区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2019NZKY-025-01),患者和参与者都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书。
讨论 本研究3例患者中,1例完全病理学缓解,1例MPR,1例残留20%肿瘤。没有因毒副作用而延迟手术,也没有严重围手术期并发症和3级及以上肺炎发生。我们的结果与其他关于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研究[6-7]相似。放射学和病理学上的缓解是不同的,持续性肿瘤肿块并不代表残留的活动性癌症。
在化疗时代,新辅助化疗联合放疗并不能改善Ⅲ/N2期NSCLC的MPR率、无事件率和总体生存率,可能的原因是常规放疗剂量不足、手术间期时间长[3]。SBRT是一种精确的放疗模型,可以显著增加辐射剂量,同时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在治疗肺癌和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方面疗效良好且优于常规放疗[8-11]。新辅助SBRT被证实耐受性良好、安全,早期NSCLC在SBRT治疗后MPR率为60%[12]。但对于Ⅲ/N2期NSCLC,需要与更有效的系统治疗相结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出现为NSCLC的治疗带来了新希望。与新辅助化疗相比,新辅助抗PD-1或抗PD-L1单药治疗早期NSCLC的MPR率更高[6,13-14]。放疗通过释放新抗原诱导免疫原性细胞死亡,上调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Ⅰ类表达和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来增强免疫应答[15-18]。在Ⅰ~Ⅲ期NSCLC患者中进行的新辅助德瓦鲁(durvalumab)单抗联合或不联合SBRT的随机2期试验[19]结果显示,durvalumab单抗联合SBRT(8 Gy×3组分)与高MPR率有关(53.3% vs. 6.7%,P<0.0001)。与本研究的一个不同之处是,50 Gy/5次的照射剂量相当于100 Gy/次的照射剂量,远高于8 Gy/3次的照射剂量(43.2 Gy)。虽然没有发生3级以上毒性反应,但是否需要如此高的放射剂量值得商榷。
对于不能切除的局部晚期NSCLC,标准胸部照射范围包括肺部病灶和肿瘤相关引流淋巴结(draining lymph node,DLN)。与此相反,在我们的研究中,对肺部病灶进行了SBRT,DLN未受到照射。主要考虑因素如下:(1)DLN是树突状细胞激活抗原特异性CD8+T细胞的主要部位[20];(2)大剂量照射肺部病变和转移的淋巴结并不能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免疫系统的高剂量辐射与第三阶段NSCLC最终治疗后的肿瘤进展和死亡相关[21-22];(3)临床前研究[23]表明,DLN的照射通过改变趋化因子的表达和CD8+T细胞的转运来抑制适应性免疫反应,所以当SBRT与免疫治疗相结合时,把DLN的放射区域排除是值得考虑的;(4)场外效率由常规放疗的10%提高到SBRT联合免疫治疗的38%[24]。对肺部病变进行SBRT治疗,不仅降低了手术难度,而且减少了放疗对淋巴结的损伤。本研究的3例患者中,患者1和患者3在新辅助治疗前通过PET/CT检查证实有淋巴结转移。新辅助治疗后,术中采集淋巴结标本未发现癌细胞。上述结果表明,即使淋巴结转移没有接受放疗,也可以获得良好的控制,这可能是免疫治疗和SBRT引起的非局部性效应导致的。
与PD-L1阳性患者相比,SBRT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PD-L1阴性患者的生存预后改善更明显。Theelen等[25]的一项Ⅱ期临床研究中,对晚期NSCLC患者的单个肿瘤病变进行了SBRT,后采用派姆单抗治疗。亚组分析表明,PD-L1阴性肿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显著延长,这表明放疗可能改变PD-L1阴性肿瘤的微环境,从而促进派姆单抗的作用。本研究中,患者2在治疗前PD-L1阴性。术后标本与细针抽吸标本相比,CD4+T细胞和CD8+T细胞计数升高。虽然患者1的PD-L1表达为80%,但将术前穿刺活检和术后标本进行比较,CD4+T细胞和CD8+T细胞并没有增加。未来需进一步评估PD-L1表达对治疗前后CD4+T细胞和CD8+T细胞的影响。
尽管SBRT联合PD-1抑制剂临床疗效较好,但联合用药可能引起重叠损伤,导致致死性重组相关免疫反应发生率高于单药治疗[26]。本研究发现特瑞普利单抗联合SBRT作为新辅助治疗几乎无副作用,该治疗没有导致手术延迟。但本研究仅在3例患者中进行了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SBRT治疗,且随访期较短。由于数据有限,未来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证实该方案的安全性和长期有效性。目前,评估新辅助免疫疗法联合放疗的前瞻性研究(NCT03237377、NCT0290495、NCT03217071和NCT02904954)在进行中,结果尚待公布。本中心也注册了类似的研究(ChiCTR2000029277)。这些研究需要长期随访,以确定新辅助免疫治疗联合放疗的安全性、长期疗效、照射范围和剂量。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王振、宋勇、申翼、强勇负责论文设计;王振、罗静、强勇负责数据整理与分析;王振、顾浩宇、罗静负责论文初稿撰写;朱熙煦、宋勇、申翼、强勇负责论文审阅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