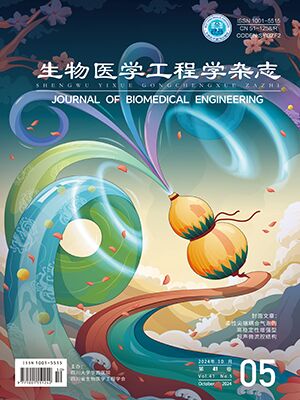颗粒物的吸入和在人体肺腺泡区的沉积可能引发肺部疾病,采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肺腺泡区吸入颗粒物的沉积状况,对肺部疾病的预防和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肺腺泡模型、模型运动方式、呼吸模式、颗粒物特性、肺部病变以及年龄等影响数值模拟结果的重要因素出发,分类总结了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的研究进展,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提出了未来发展重点研究的方向,以期为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的进一步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引用本文: 李鹏辉, 李蓉, 乔扬, 徐新喜. 人体肺腺泡区吸入颗粒物沉积状况数值模拟的研究进展.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19, 36(3): 499-503. doi: 10.7507/1001-5515.201808001 复制
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细颗粒物和病毒气溶胶能够通过呼吸作用进入人体,在肺腺泡区扩散、沉积,进而刺激、侵蚀肺组织,损害肺功能,诱发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1]、肺气肿等多种肺部疾病。因此,研究肺腺泡区吸入颗粒物的沉积状况对探究肺部疾病致病机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医学手段只能获得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的总沉积率,对其在肺腺泡区的运动规律无从了解,而建立计算机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2],因而被国内外诸多学者广泛采用。其中,肺腺泡模型、模型运动方式、呼吸模式、颗粒物特性、肺部病变和年龄等因素能够显著影响数值模拟结果。本文以这些因素为基准,分类总结了近年来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的研究进展,分析了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提出了未来发展的研究重点,以期为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的进一步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1 肺腺泡模型
如图 1 所示,肺腺泡是指终末细支气管以下的肺组织,包括呼吸性细支气管、肺泡管、肺泡囊和肺泡,是呼吸作用的主要区域。在经典的全肺模型(Weibel A 模型[3])中,肺部分为 0~23 级,17 级及以下部分为肺腺泡区。人体肺腺泡区结构极其复杂,几何尺寸小至微米级,目前尚未获得真实的计算机模型。因此,国内外学者进行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研究时采用的模型均经过大量简化,包括单肺泡模型和多肺泡模型[4]。
 图1
人体肺腺泡结构
Figure1.
Human pulmonary acinar geometry
图1
人体肺腺泡结构
Figure1.
Human pulmonary acinar geometry
单肺泡模型仅对单个肺泡建模,能以较小的计算量获得肺泡内流场形态和颗粒物沉积状况。Talaat 等[5]将肺泡囊简化为球状单肺泡模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肺泡内流场和颗粒物状态与呼吸道、肺泡管等区域存在较大差异,肺泡内无循环流、颗粒物沉积所需时间也更长。Sznitman 等[6]建立了 9 个处于不同级数的单肺泡模型,发现肺泡内流场形态主要受所处级数影响,随着级数增加肺泡内流场形态由循环状向辐射状变化。
对单个肺泡建模只能探究肺泡内部特性,因此,国内外学者纷纷尝试采用各种方法构建多肺泡模型以进一步探究肺腺泡区特性。多肺泡模型主要分为四类:“柱状气管+球状肺泡”的多肺泡模型、基于十四面体的多肺泡模型、泰森多边形法构建的多肺泡模型、计算机成像和重建技术构建的多肺泡模型。“柱状气管+球状肺泡”的多肺泡模型架构源自于 Weibel A 模型[3],模型中细支气管简化为柱状空心长管,肺泡简化为附在长管外壁、朝内开口的空心半球。李振振[7]采用“柱状气管+球状肺泡”架构建立了每级只有一个肺泡的 8 级肺腺泡模型,发现随着肺腺泡级数的增加,肺泡内流场形态从循环状向放射状变化,颗粒物沉积率也逐渐增大,与 Sznitman 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类模型结构简单,适应性强,细支气管长度、管径、分叉角和肺泡半径等参数可调,可依据研究目标调整建立适当的模型,因而被国内外学者所广泛采用。Fung[8]认为十四面体外观与人体肺泡形态学结构更为一致,首次采用十四面体构建了多肺泡模型,该模型填充效果好,肺泡形状、肺腺管长度、分叉角等都与 Haefeli-Bleuer 等[9]的测量数据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因而也获得了较多研究人员的认可[10-15]。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模型中肺泡大小一致,与人体实际有较大差异。以 Katan 等[12]建立的十四面体多肺泡模型为例,该模型共 6 级,包含 277 个大小一致的十四面体,而人体真实肺泡随级数增加而增大(如 17 级肺泡平均半径为 106 μm,23 级处则为 190 μm[3]),由于肺泡尺寸对肺泡内流场形态有较大影响[6],因而该模型仅适用于肺泡大小一致或变化量可忽略不计的情况。
上述模型均为人工建模,结构相对简单、简化程度较大,因而另有一些学者尝试采用计算机算法构建更加真实的肺腺泡模型。泰森多边形法是用于建筑、工业结构设计的一种计算机算法。Koshiyama 等[16]率先将泰森多边形法应用于大鼠肺腺泡模型构建过程中,生成模型中肺泡大小、个数和细支气管结构等参数与 Mercer 等[17]报道的数据具有很好的一致性。Hofemeier 等[18]进一步采用该方法建立了人体肺腺泡模型,该模型共 14 级,肺泡数量超过 2 000 个,是目前肺泡数量最多的人体肺腺泡模型,为肺腺泡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
但是,就整个肺腺泡而言,肺泡数量多达数亿个、细支气管结构异常复杂,因此要通过建模得到真实肺腺泡模型几乎不可能。而计算机成像和重建技术的发展为获得更加真实的肺腺泡模型提供了新视角。Sera 等[19]采用微计算机断层扫描(microfocal computed tomography system,micro-CT)技术重构了大鼠肺腺泡模型,发现细颗粒物在肺腺泡中部和末端沉积量更多。Puliyakote 等[20]详细地给出了多分辨率微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multi- resolution micro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技术重构大鼠肺腺泡模型的方法和过程,并提出将大型哺乳动物肺组织分割成小块逐个建模、拼接以获得其真实肺腺泡模型的想法,为获得人体肺腺泡真实模型提供了新思路。由于计算机成像技术分辨率有限,且人体肺腺泡结构过于复杂,因而构建更加真实的人体肺腺泡模型仍然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挑战。
2 模型运动方式
大量研究表明,模型运动方式对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是显著的,常见的模型运动方式包括刚性固定、各向同性运动、各向异性运动。
模型刚性固定操作简单、计算量小,常见于肺腺泡区早期研究和与其他运动方式的对比研究中。各向同性运动是目前采用最为广泛的模型运动方式,利用模型扩张收缩运动模拟人体肺腺泡的运动,模型运动过程中形状不变,具有自相似性。以黄俊[21]的研究为例,他对比研究了肺泡刚性固定和各向同性运动对内部流场和颗粒相的影响,发现肺泡运动产生的对流现象对亚微米颗粒的作用要远大于布朗力,因而亚微米颗粒更容易在弹性肺泡中沉积。Talaat 等[5]认为正常呼吸状态下人体肺部运动并非各向同性,建立了 X、Y、Z 三个方向运动量之比为 1: 0.375: 1 的各向异性运动单肺泡模型,对比研究了模型不同运动方式对颗粒物运动规律的影响,发现运动模型中颗粒物沉积速度更快、沉积量更少,而各向同性与各向异性运动对结果影响并不明显。Hofemeier 等[13]研究了 6 级十四面体多肺泡模型各向同性和三类各向异性运动下颗粒物的沉积状况,发现模型运动方式的不同仅对 0.5~0.75 μm 的颗粒物沉积状况影响较大。以上研究表明,模型运动引起的对流现象能加速内部颗粒物沉积,而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运动对颗粒物运动规律的影响尚不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肺腺泡刚性固定和主动运动的条件设置与人体实际情况依然有较大差异,肺腺泡运动应该是胸腔扩张、收缩作用下的被动变形。因此,一些学者尝试着将肺部压强变化、气流与肺腺泡壁的流固耦合作用考虑进肺腺泡区的研究中。Iranica 等[22]在肺泡囊薄壁模型外部施加正弦变化的压力,研究了流固耦合作用下肺泡囊壁的力学特性和内部流场特性,发现模型薄壁部分压力较大,易引发肺气肿的发生。流固耦合作用更加符合人体呼吸作用机制,在研究肺腺泡区流场特性、颗粒物运动规律的同时兼顾固体组织的力学特性,可以通过改变固体组织的参数模拟肺腺泡病变(如肺气肿等)对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进而为探究相关疾病的致病机制和治疗方法提供更深层次的参考。Aghasafari 等[23]研究了流固耦合作用下肺泡囊的张力分布,发现肺泡连接处和肺泡囊中部张力较大,进而提出张力较大区域炎症发生率更高的结论。但目前考虑流固耦合效应的研究还太少,仅有少量二维和简单的三维模型,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 呼吸模式
颗粒物在肺腺泡区沉积机制主要包括惯性冲击、重力沉降和布朗扩散。呼吸作用是肺腺泡区颗粒物惯性运动的主要动力源,也是影响颗粒物沉积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Haidl 等[24]综合分析了大量药物吸入治疗数据,发现呼吸频率、潮气量、吸气时间等都会显著影响药物吸入治疗效果。Horváth 等[25]研究发现,患者在屏气时能大幅度增加药物颗粒的沉积率,屏气 5 s 可使沉积率增加 11.3%~26.5%,屏气 25 s 沉积率增加 20.7%~53%。Talaat 等[5]对比了 5 种不同频率呼吸模式下颗粒物的沉积状况,发现呼吸频率越快,颗粒物沉积率越低,相应的沉积时间越短。Hofemeier 等[18]研究了普通呼吸模式(潮气量为 500 mL)和深呼吸模式(潮气量为 2 500 mL)下的颗粒物沉积状况,发现深呼吸模式下颗粒物在肺腺泡内总体沉积率更高,肺泡/肺泡管沉积率之比也更大。综上所述,呼吸模式对肺腺泡区颗粒物沉积状况的影响规律可以基本概括为:① 屏气能显著增加颗粒物沉积率;② 呼吸频率越快,颗粒物沉积率越低;③ 潮气量越大,颗粒物沉积率越高。
4 颗粒物特性
颗粒物特性方面,主要研究颗粒物粒径、密度、形状、生物特性等对其沉积状况的影响。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研究中颗粒物多被简化为球状以研究其粒径对沉积部位和沉积率的影响。Hofemeier 等[13]研究了 0.005~5.0 μm 粒径范围内颗粒物沉积状况,发现颗粒物沉积曲线呈“U”型,即随着颗粒物粒径增加,沉积率先减小后增加,在 1 μm 左右达到最小沉积率。这是因为布朗扩散和重力沉降是影响颗粒物沉积特性的重要因素,随着颗粒物粒径增加,布朗力作用减小、重力作用增加[19]。细微颗粒沉积由布朗力主导,较大颗粒沉积由重力沉降主导,而粒径 1 μm 左右的颗粒物两者作用都较弱,因此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现象。于申等[26]研究了 2.5、5、10 μm 三种颗粒物沉积率与密度的关系,发现颗粒物密度增大,重力作用增加,其沉积率也随之增加,充分证明了重力沉积对大颗粒物的主导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力方向的改变仅仅改变颗粒物的沉积位置,对沉积率基本无影响[10, 27]。Shachar-Berman 等[28]研究了非球状颗粒在振动圆管中的沉积状况,发现椭球状颗粒的运动轨迹更加复杂、受到的黏性阻力更大、滞空时间也更长,说明颗粒物形状应该作为沉积重要因素进行分析。Sturm[29]认为生物气溶胶的形状、生物物理特性与球状颗粒差异更大,因此在进行生物气溶胶数值模拟研究中应充分考虑其形态学差异产生的影响。Ostrovski 等[15]研究发现在颗粒物中加入磁性粒子能使 0.5~3.0 μm 粒径的颗粒物在肺腺泡区沉积率大大提高。以上研究表明,颗粒物粒径、密度、形状、生物特性等因素都会对其在肺腺泡区的沉积状况产生显著影响,应进一步关注其影响规律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5 肺部病变和年龄
肺部病变如 COPD、肺气肿、肺纤维等能对肺腺泡结构造成改变,不同年龄人群肺腺泡结构也具有明显差异,因此研究肺部病变和年龄对肺腺泡结构产生的改变以及结构改变对颗粒物沉积状况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Oakes 等[11]建立了基于十四面体的多肺泡模型,通过增加肺泡数量、去除肺泡间隔的方式构建了肺气肿模型,发现肺气肿模型内颗粒物沉积区域更加分散、沉积率也相对更低。Sturm[30]根据临床不同类型的肺气肿疾病特征构建了对应的二维肺气肿模型,研究了不同模型中药物颗粒的扩散规律,发现不同肺气肿模型中扩散程度存在差异,但均比健康模型更加分散。这是因为肺气肿模型体积较大,颗粒物沉积路径增长,因而沉积位置分散,沉积率较小。Aghasafari 等[31]将流感病毒入侵对肺腺泡结构的改变简化为部分肺泡的坍塌,发现病变模型中气流流速和压力降低。此外,该研究还认为开展肺部病变深入研究时应考虑气流与模型的流固耦合效应。
由于不同年龄人群肺腺泡结构的不同[7, 12, 14],颗粒物肺部沉积率也存在明显差异。以 Katan 等[12]的研究为例,3 月、1 岁零 9 月、3 岁儿童和成年人肺腺泡模型体积分别为 30、81、155、500 mL,年龄越小颗粒物沉积率越高。这是因为年幼儿童肺腺泡模型尺寸更小,颗粒物沉积路径减短,因而更有利于颗粒物的沉积。以上研究初步探讨了肺部病变和年龄对肺腺泡结构和内部颗粒物运动规律产生的影响,但模型简化程度过大,且考虑的疾病种类过于单一,仍需进一步研究。
6 未来研究重点
颗粒物在肺腺泡区沉积数值模拟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多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肺腺泡模型、模型运动方式、呼吸模式、颗粒物特性、肺部病变和年龄等特定因素对沉积结果的影响。但受限于人体肺腺泡的复杂性和计算机建模技术的不足,现行研究中数值模拟的精准度和可信度还有待提高。综上所述,颗粒物肺腺泡区沉积数值模拟的未来研究重点应包括:
(1)采用合适的计算机智能算法以及成像、建模等技术辅助构建更加真实的肺腺泡模型。现今肺腺泡模型与实际差异过大,而真实的肺腺泡模型是相关研究的基础。
(2)关注肺腺泡区生物特性的影响,如细支气管和肺泡的黏弹性、肺泡间作用[32]、气体交换等。受限于计算机建模和仿真技术的局限,以往研究未考虑肺腺泡区生物特性对结果的影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有助于建立更完善的肺腺泡区动力学机制。
(3)关注颗粒物的力学特征(如吸附性、粘性)、生物活性(如毒性、繁殖)以及相互作用(如碰撞、附着)的影响,扩大颗粒物的研究范围(如液滴、花粉、病毒、细菌等气溶胶颗粒)以进一步探究颗粒物致病机制和治疗手段。
(4)扩大肺部疾病关注范围(如肺纤维、炎症、肺结核、肿瘤等),结合病理构建更真实的肺部病变模型以得出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结果和理论。
(5)数值模拟结果正确性验证。现行研究多与文献数据进行对比,应建立可参照的体外实验或动物实验对比研究,论证结果正确性。
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细颗粒物和病毒气溶胶能够通过呼吸作用进入人体,在肺腺泡区扩散、沉积,进而刺激、侵蚀肺组织,损害肺功能,诱发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1]、肺气肿等多种肺部疾病。因此,研究肺腺泡区吸入颗粒物的沉积状况对探究肺部疾病致病机制、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医学手段只能获得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的总沉积率,对其在肺腺泡区的运动规律无从了解,而建立计算机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2],因而被国内外诸多学者广泛采用。其中,肺腺泡模型、模型运动方式、呼吸模式、颗粒物特性、肺部病变和年龄等因素能够显著影响数值模拟结果。本文以这些因素为基准,分类总结了近年来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的研究进展,分析了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提出了未来发展的研究重点,以期为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的进一步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1 肺腺泡模型
如图 1 所示,肺腺泡是指终末细支气管以下的肺组织,包括呼吸性细支气管、肺泡管、肺泡囊和肺泡,是呼吸作用的主要区域。在经典的全肺模型(Weibel A 模型[3])中,肺部分为 0~23 级,17 级及以下部分为肺腺泡区。人体肺腺泡区结构极其复杂,几何尺寸小至微米级,目前尚未获得真实的计算机模型。因此,国内外学者进行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研究时采用的模型均经过大量简化,包括单肺泡模型和多肺泡模型[4]。
 图1
人体肺腺泡结构
Figure1.
Human pulmonary acinar geometry
图1
人体肺腺泡结构
Figure1.
Human pulmonary acinar geometry
单肺泡模型仅对单个肺泡建模,能以较小的计算量获得肺泡内流场形态和颗粒物沉积状况。Talaat 等[5]将肺泡囊简化为球状单肺泡模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肺泡内流场和颗粒物状态与呼吸道、肺泡管等区域存在较大差异,肺泡内无循环流、颗粒物沉积所需时间也更长。Sznitman 等[6]建立了 9 个处于不同级数的单肺泡模型,发现肺泡内流场形态主要受所处级数影响,随着级数增加肺泡内流场形态由循环状向辐射状变化。
对单个肺泡建模只能探究肺泡内部特性,因此,国内外学者纷纷尝试采用各种方法构建多肺泡模型以进一步探究肺腺泡区特性。多肺泡模型主要分为四类:“柱状气管+球状肺泡”的多肺泡模型、基于十四面体的多肺泡模型、泰森多边形法构建的多肺泡模型、计算机成像和重建技术构建的多肺泡模型。“柱状气管+球状肺泡”的多肺泡模型架构源自于 Weibel A 模型[3],模型中细支气管简化为柱状空心长管,肺泡简化为附在长管外壁、朝内开口的空心半球。李振振[7]采用“柱状气管+球状肺泡”架构建立了每级只有一个肺泡的 8 级肺腺泡模型,发现随着肺腺泡级数的增加,肺泡内流场形态从循环状向放射状变化,颗粒物沉积率也逐渐增大,与 Sznitman 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该类模型结构简单,适应性强,细支气管长度、管径、分叉角和肺泡半径等参数可调,可依据研究目标调整建立适当的模型,因而被国内外学者所广泛采用。Fung[8]认为十四面体外观与人体肺泡形态学结构更为一致,首次采用十四面体构建了多肺泡模型,该模型填充效果好,肺泡形状、肺腺管长度、分叉角等都与 Haefeli-Bleuer 等[9]的测量数据具有很好的一致性,因而也获得了较多研究人员的认可[10-15]。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模型中肺泡大小一致,与人体实际有较大差异。以 Katan 等[12]建立的十四面体多肺泡模型为例,该模型共 6 级,包含 277 个大小一致的十四面体,而人体真实肺泡随级数增加而增大(如 17 级肺泡平均半径为 106 μm,23 级处则为 190 μm[3]),由于肺泡尺寸对肺泡内流场形态有较大影响[6],因而该模型仅适用于肺泡大小一致或变化量可忽略不计的情况。
上述模型均为人工建模,结构相对简单、简化程度较大,因而另有一些学者尝试采用计算机算法构建更加真实的肺腺泡模型。泰森多边形法是用于建筑、工业结构设计的一种计算机算法。Koshiyama 等[16]率先将泰森多边形法应用于大鼠肺腺泡模型构建过程中,生成模型中肺泡大小、个数和细支气管结构等参数与 Mercer 等[17]报道的数据具有很好的一致性。Hofemeier 等[18]进一步采用该方法建立了人体肺腺泡模型,该模型共 14 级,肺泡数量超过 2 000 个,是目前肺泡数量最多的人体肺腺泡模型,为肺腺泡模型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
但是,就整个肺腺泡而言,肺泡数量多达数亿个、细支气管结构异常复杂,因此要通过建模得到真实肺腺泡模型几乎不可能。而计算机成像和重建技术的发展为获得更加真实的肺腺泡模型提供了新视角。Sera 等[19]采用微计算机断层扫描(microfocal computed tomography system,micro-CT)技术重构了大鼠肺腺泡模型,发现细颗粒物在肺腺泡中部和末端沉积量更多。Puliyakote 等[20]详细地给出了多分辨率微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multi- resolution micro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技术重构大鼠肺腺泡模型的方法和过程,并提出将大型哺乳动物肺组织分割成小块逐个建模、拼接以获得其真实肺腺泡模型的想法,为获得人体肺腺泡真实模型提供了新思路。由于计算机成像技术分辨率有限,且人体肺腺泡结构过于复杂,因而构建更加真实的人体肺腺泡模型仍然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挑战。
2 模型运动方式
大量研究表明,模型运动方式对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是显著的,常见的模型运动方式包括刚性固定、各向同性运动、各向异性运动。
模型刚性固定操作简单、计算量小,常见于肺腺泡区早期研究和与其他运动方式的对比研究中。各向同性运动是目前采用最为广泛的模型运动方式,利用模型扩张收缩运动模拟人体肺腺泡的运动,模型运动过程中形状不变,具有自相似性。以黄俊[21]的研究为例,他对比研究了肺泡刚性固定和各向同性运动对内部流场和颗粒相的影响,发现肺泡运动产生的对流现象对亚微米颗粒的作用要远大于布朗力,因而亚微米颗粒更容易在弹性肺泡中沉积。Talaat 等[5]认为正常呼吸状态下人体肺部运动并非各向同性,建立了 X、Y、Z 三个方向运动量之比为 1: 0.375: 1 的各向异性运动单肺泡模型,对比研究了模型不同运动方式对颗粒物运动规律的影响,发现运动模型中颗粒物沉积速度更快、沉积量更少,而各向同性与各向异性运动对结果影响并不明显。Hofemeier 等[13]研究了 6 级十四面体多肺泡模型各向同性和三类各向异性运动下颗粒物的沉积状况,发现模型运动方式的不同仅对 0.5~0.75 μm 的颗粒物沉积状况影响较大。以上研究表明,模型运动引起的对流现象能加速内部颗粒物沉积,而各向同性和各向异性运动对颗粒物运动规律的影响尚不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肺腺泡刚性固定和主动运动的条件设置与人体实际情况依然有较大差异,肺腺泡运动应该是胸腔扩张、收缩作用下的被动变形。因此,一些学者尝试着将肺部压强变化、气流与肺腺泡壁的流固耦合作用考虑进肺腺泡区的研究中。Iranica 等[22]在肺泡囊薄壁模型外部施加正弦变化的压力,研究了流固耦合作用下肺泡囊壁的力学特性和内部流场特性,发现模型薄壁部分压力较大,易引发肺气肿的发生。流固耦合作用更加符合人体呼吸作用机制,在研究肺腺泡区流场特性、颗粒物运动规律的同时兼顾固体组织的力学特性,可以通过改变固体组织的参数模拟肺腺泡病变(如肺气肿等)对数值模拟结果的影响,进而为探究相关疾病的致病机制和治疗方法提供更深层次的参考。Aghasafari 等[23]研究了流固耦合作用下肺泡囊的张力分布,发现肺泡连接处和肺泡囊中部张力较大,进而提出张力较大区域炎症发生率更高的结论。但目前考虑流固耦合效应的研究还太少,仅有少量二维和简单的三维模型,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 呼吸模式
颗粒物在肺腺泡区沉积机制主要包括惯性冲击、重力沉降和布朗扩散。呼吸作用是肺腺泡区颗粒物惯性运动的主要动力源,也是影响颗粒物沉积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Haidl 等[24]综合分析了大量药物吸入治疗数据,发现呼吸频率、潮气量、吸气时间等都会显著影响药物吸入治疗效果。Horváth 等[25]研究发现,患者在屏气时能大幅度增加药物颗粒的沉积率,屏气 5 s 可使沉积率增加 11.3%~26.5%,屏气 25 s 沉积率增加 20.7%~53%。Talaat 等[5]对比了 5 种不同频率呼吸模式下颗粒物的沉积状况,发现呼吸频率越快,颗粒物沉积率越低,相应的沉积时间越短。Hofemeier 等[18]研究了普通呼吸模式(潮气量为 500 mL)和深呼吸模式(潮气量为 2 500 mL)下的颗粒物沉积状况,发现深呼吸模式下颗粒物在肺腺泡内总体沉积率更高,肺泡/肺泡管沉积率之比也更大。综上所述,呼吸模式对肺腺泡区颗粒物沉积状况的影响规律可以基本概括为:① 屏气能显著增加颗粒物沉积率;② 呼吸频率越快,颗粒物沉积率越低;③ 潮气量越大,颗粒物沉积率越高。
4 颗粒物特性
颗粒物特性方面,主要研究颗粒物粒径、密度、形状、生物特性等对其沉积状况的影响。肺腺泡区数值模拟研究中颗粒物多被简化为球状以研究其粒径对沉积部位和沉积率的影响。Hofemeier 等[13]研究了 0.005~5.0 μm 粒径范围内颗粒物沉积状况,发现颗粒物沉积曲线呈“U”型,即随着颗粒物粒径增加,沉积率先减小后增加,在 1 μm 左右达到最小沉积率。这是因为布朗扩散和重力沉降是影响颗粒物沉积特性的重要因素,随着颗粒物粒径增加,布朗力作用减小、重力作用增加[19]。细微颗粒沉积由布朗力主导,较大颗粒沉积由重力沉降主导,而粒径 1 μm 左右的颗粒物两者作用都较弱,因此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现象。于申等[26]研究了 2.5、5、10 μm 三种颗粒物沉积率与密度的关系,发现颗粒物密度增大,重力作用增加,其沉积率也随之增加,充分证明了重力沉积对大颗粒物的主导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力方向的改变仅仅改变颗粒物的沉积位置,对沉积率基本无影响[10, 27]。Shachar-Berman 等[28]研究了非球状颗粒在振动圆管中的沉积状况,发现椭球状颗粒的运动轨迹更加复杂、受到的黏性阻力更大、滞空时间也更长,说明颗粒物形状应该作为沉积重要因素进行分析。Sturm[29]认为生物气溶胶的形状、生物物理特性与球状颗粒差异更大,因此在进行生物气溶胶数值模拟研究中应充分考虑其形态学差异产生的影响。Ostrovski 等[15]研究发现在颗粒物中加入磁性粒子能使 0.5~3.0 μm 粒径的颗粒物在肺腺泡区沉积率大大提高。以上研究表明,颗粒物粒径、密度、形状、生物特性等因素都会对其在肺腺泡区的沉积状况产生显著影响,应进一步关注其影响规律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
5 肺部病变和年龄
肺部病变如 COPD、肺气肿、肺纤维等能对肺腺泡结构造成改变,不同年龄人群肺腺泡结构也具有明显差异,因此研究肺部病变和年龄对肺腺泡结构产生的改变以及结构改变对颗粒物沉积状况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Oakes 等[11]建立了基于十四面体的多肺泡模型,通过增加肺泡数量、去除肺泡间隔的方式构建了肺气肿模型,发现肺气肿模型内颗粒物沉积区域更加分散、沉积率也相对更低。Sturm[30]根据临床不同类型的肺气肿疾病特征构建了对应的二维肺气肿模型,研究了不同模型中药物颗粒的扩散规律,发现不同肺气肿模型中扩散程度存在差异,但均比健康模型更加分散。这是因为肺气肿模型体积较大,颗粒物沉积路径增长,因而沉积位置分散,沉积率较小。Aghasafari 等[31]将流感病毒入侵对肺腺泡结构的改变简化为部分肺泡的坍塌,发现病变模型中气流流速和压力降低。此外,该研究还认为开展肺部病变深入研究时应考虑气流与模型的流固耦合效应。
由于不同年龄人群肺腺泡结构的不同[7, 12, 14],颗粒物肺部沉积率也存在明显差异。以 Katan 等[12]的研究为例,3 月、1 岁零 9 月、3 岁儿童和成年人肺腺泡模型体积分别为 30、81、155、500 mL,年龄越小颗粒物沉积率越高。这是因为年幼儿童肺腺泡模型尺寸更小,颗粒物沉积路径减短,因而更有利于颗粒物的沉积。以上研究初步探讨了肺部病变和年龄对肺腺泡结构和内部颗粒物运动规律产生的影响,但模型简化程度过大,且考虑的疾病种类过于单一,仍需进一步研究。
6 未来研究重点
颗粒物在肺腺泡区沉积数值模拟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多从不同角度出发研究肺腺泡模型、模型运动方式、呼吸模式、颗粒物特性、肺部病变和年龄等特定因素对沉积结果的影响。但受限于人体肺腺泡的复杂性和计算机建模技术的不足,现行研究中数值模拟的精准度和可信度还有待提高。综上所述,颗粒物肺腺泡区沉积数值模拟的未来研究重点应包括:
(1)采用合适的计算机智能算法以及成像、建模等技术辅助构建更加真实的肺腺泡模型。现今肺腺泡模型与实际差异过大,而真实的肺腺泡模型是相关研究的基础。
(2)关注肺腺泡区生物特性的影响,如细支气管和肺泡的黏弹性、肺泡间作用[32]、气体交换等。受限于计算机建模和仿真技术的局限,以往研究未考虑肺腺泡区生物特性对结果的影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有助于建立更完善的肺腺泡区动力学机制。
(3)关注颗粒物的力学特征(如吸附性、粘性)、生物活性(如毒性、繁殖)以及相互作用(如碰撞、附着)的影响,扩大颗粒物的研究范围(如液滴、花粉、病毒、细菌等气溶胶颗粒)以进一步探究颗粒物致病机制和治疗手段。
(4)扩大肺部疾病关注范围(如肺纤维、炎症、肺结核、肿瘤等),结合病理构建更真实的肺部病变模型以得出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结果和理论。
(5)数值模拟结果正确性验证。现行研究多与文献数据进行对比,应建立可参照的体外实验或动物实验对比研究,论证结果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