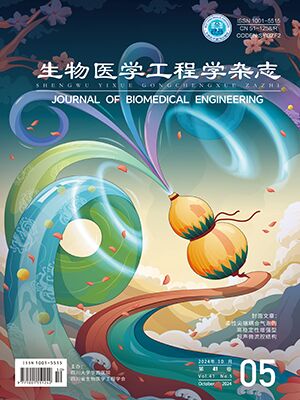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沉积是很多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的主要诱因。通过建立计算机或体外实体模型研究颗粒物在呼吸系统内的沉积规律,对相关的疾病预防与治疗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目前学者们对各种模型的上呼吸道及肺腺泡区的可吸入颗粒物沉积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分析,阐述了这些研究结果在疾病成因分析、吸入给药治疗等方面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应用局限性,并指出了未来重点研究方向,对于指导可吸入颗粒物沉积模拟、实验和应用方面进一步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引用本文: 李蓉, 赵秀国, 刘亚军, 徐新喜. 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沉积的数值模拟与实验研究进展.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17, 34(4): 637-642. doi: 10.7507/1001-5515.201610022 复制
引言
呼吸系统是空气中颗粒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颗粒物进入人体呼吸系统可能诱发肺癌、引起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带有致病微生物的颗粒物更是肺炎、结核、流感等各类传染病传播的主要方式。普遍认为,颗粒物直径越小,进入呼吸系统部位越深,超细颗粒物甚至能够穿透肺泡进入人体血液循环,从而导致心脑血管等相关疾病[1]。早在 1993 年,Dockery 等[2]对美国 6 个城市的 PM2.5 颗粒物(指平均粒径为 2.5 μm 的颗粒物)暴露健康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浓度每升高 10 μg/m3,心肺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均提高 18%。近年来的流行病学研究已证实,颗粒物浓度增加与呼吸系统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具有很强的相关性[3]。
大量解剖学和病理学研究表明,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的沉积部位与沉积量(一定时间内沉积在特定呼吸部位的颗粒物数量)[4]。因此,研究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沉积规律对于定量研究颗粒物的暴露风险及剂量健康效应至关重要。但由于采用志愿者只能获得呼吸系统总沉积率,而无法确定肺部各个部位的沉积差异,因此,国内外诸多学者采用模拟仿真法和实体实验模型法开展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介绍近年来人体鼻咽区、支气管区和肺腺泡区的模拟仿真和实验研究方法、结果,阐述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以指导可吸入颗粒物沉积模拟、实验和应用方面进一步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与指导价值。
1 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鼻咽区沉积
人体鼻咽区包括鼻腔和咽喉,是可吸入颗粒物首先进入人体的区域,由于结构复杂,内含粘膜和纤毛,对颗粒物随后进入气管和肺部的影响很大[5]。苏英锋等[6]对健康人鼻腔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成像后研究,发现气流在鼻腔内主要为层流,而上颌窦腔内气流则以自由扩散为主。Cisonni 等[7]构建人体鼻腔三维计算模型,研究虚拟钩突切除前后可吸入颗粒物的沉积情况,发现在进行了上颌窦手术后,患者通气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鼻窦区吸入纳米/微米级颗粒物的沉积明显增加。Xi 等[8]研究发现,人体喉部声门区的截面积变大将增大颗粒物在鼻咽区的沉积。以上研究表明,鼻咽部结构的变化明显影响此区域的可吸入颗粒物沉积。特别是增大呼吸截面积,可提高可吸入颗粒物在鼻咽区的沉积率。这对于预防可吸入颗粒物进一步在气管、支气管和肺腺泡区的沉积,提供了一种临床可操作的思路。黄小青等[9]研究了高速气流对人体鼻腔温度场影响,发现急促呼吸时鼻腔对呼吸温度场升温功能下降,从而影响整个呼吸系统的沉积。总之,鼻咽区是可吸入颗粒物进入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屏障,其结构和呼吸方式对气管支气管的气流和颗粒物向肺部深处输送具有较大的影响。
2 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支气管沉积
支气管区域是目前人体呼吸系统中可吸入颗粒物沉积研究的焦点,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呼吸模式、颗粒物属性等对沉积率的影响,研究方法包括计算机仿真和实体实验模型等。
呼吸方式方面,Van Rhein等[10]研究了不同呼吸流量波形对沉积的影响,发现斜波、方波的沉积率比正弦波要高 43.65%,说明呼吸模式对可吸入颗粒物在支气管区沉降的重要影响。Sracic 等[11]研究了运动时 PM2.5 颗粒物的吸入沉积规律,发现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支气管区域总的沉积率随着运动强度而增加,说明剧烈运动时 PM2.5 沉积明显增大。Augusto 等[12]研究了睡眠、休息、适度的活动和激烈运动模式下粒径 1~3 μm 的颗粒物在前 4 级支气管内的沉积规律,发现不同模式下由重力引起的沉积之间差异最大可达 172%,布朗扩散沉积差异最大为 11%,进一步阐明呼吸模式影响沉积的本质是重力沉积影响。而在模拟条件方面,主要进行的是呼吸流量和颗粒物直径方面的影响研究。Islam 等[13]采用 CT 扫描技术建立上呼吸道数值计算模型,并对不同呼吸流量下颗粒物沉降的情况进行模拟研究,结论是流量越大沉降率越高,表明颗粒物沉积受支气管气流影响较为明显。
颗粒物特性方面,主要研究颗粒物形状、密度、大小、生物特性等。Rahimi-Gorji 等[14-15]研究表明,5~10 μm 颗粒物在呼吸流量为 30 L/min 时沉积率最高,而 1 μm 颗粒物则在 15 L/min 时最大,说明不同粒径的可吸入颗粒物受惯性碰撞影响不同。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呼吸流量增大,沉积向高级支气管迁移。Lintermann 等[16]研究表明,粒径 2.5~10 μm 的颗粒物仅有 0.69% 沉积在前 6 级支气管上,说明这一范围的颗粒物大部分进入到肺部更深处,可能带来更大的健康威胁。Darquenne 等[17]还研究了重力沉积效应对颗粒物沉积的影响,发现 0.5~3 μm 的颗粒物沉积率随密度增大而明显增大。而对于颗粒物本身通常需考虑其密度对沉积的影响,于申等[18]研究了不同密度的颗粒物沉积规律,发现随着密度的增大,颗粒物沉积率有所上升,且粒径越大,上升效果越明显。以上研究表明,重力是影响颗粒物在支气管区域沉积的重要因素。
目前,有学者对一些特殊颗粒物在支气管区域的沉积规律进行了研究。Dastan 等[19]研究了非圆形颗粒物在鼻腔中的沉积规律,认为颗粒物长径比应作为一个重要参数进行分析。Sturm[20]研究了纳米级超细颗粒物的运动轨迹以及沉积方式,研究表明纳米级颗粒物与微米级颗粒物的沉积形态包括沉积机理都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重力引起的惯性碰撞处于次要地位,主要沉积因素是扩散。因此在进行计算机仿真分析时,应根据所模拟的颗粒物直径选择相应的流体力学方程和算法。生物气溶胶颗粒物在形态学上更具有多样化特征,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生物颗粒物形状和呼吸条件对生物气溶胶沉积的影响最大[21],因此在研究生物气溶胶沉积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Winkler-Heil 等[22]研究了吸湿性颗粒物 NaCl 在人体呼吸系统的沉积。结果表明,由于呼吸系统的加湿作用,导致了 NaCl 吸水后重量和表面性质发生变化,从而降低了直径 0.1~0.7 μm 颗粒物的沉积率。这些研究充分表明,颗粒物形状、大小、表面特性以及生物学因素都会对其在呼吸系统内的沉积带来直接影响。
随着计算机建模技术的进步,研究者致力于建立更全面更接近真实的计算机模型。Kabilan 等[23]采用微计算机断层扫描(micron computed tomo- graphy,Micro-CT)成像技术,建立了 500 μm 级别的细末支气管模型,支气管出口达到 272 个。研究结果表明,粒径 1 μm 的颗粒物有 5.7% 沉积在支气管和细支气管。值得注意的是,Kabilan 等[23]还对建立的拥有 2 878 个支气管的大兔计算机模型进行分析,并与实体实验模型进行对比,发现计算机仿真结果与实体模型放射性实验结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该结果说明,即使建立的计算机仿真模型已相当接近真实,但与实际情况仍有较大差异。Islam 等[24]采用拓扑结构建立了包含 1 453 个支气管的复杂模型,是目前文献报道中支气管数目最多的计算机三维仿真模型,他们利用该模型研究了不同呼吸流量和颗粒物粒径对支气管沉积的影响,发现右肺支气管比左肺支气管沉积率更高,这可能是由于人体左右肺的结构差异造成的。
计算机仿真往往将可吸入颗粒物和人体呼吸系统进行理想化假设,因此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之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差异。又由于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沉积后无法直接采样,放射成像法只能得到大致的数值,且放射剂量对人体具有潜在的健康威胁,因此尚未出现采用人体试验的方法研究呼吸系统的沉积效率。研究者们只有尝试通过构建体外实验模型来验证计算机仿真的结果。Borojeni 等[25]采用 CT 和三维(three dimension,3D)打印技术建立了成年人和儿童的 5 级支气管丙烯酸塑料实体模型,实验结果与以往发表过的经验模型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实验数据虽然具有较大的发散性,但整体趋势与理论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说明实体模型是研究可吸入颗粒物沉积的可行方法。李福生等[26]建立了包括口腔、悬雍垂、咽部、会厌、喉部、声门、梨状窝、气管和前 3 级支气管的实体模型,在模型内壁涂抹硅油模拟呼吸道壁面黏性,研究结果表明,粒径为 6.5 μm 的颗粒物在气管和前 3 级沉积率达 29%,而 Rahimi-Gorji 等[14]计算机仿真的结果为 19%,二者相差较大。由于目前实体模型方面的研究较少,尚无法得出其与计算机模型能否相互验证,或者哪一种方法更接近于真实的结论。
过去十余年,可吸入颗粒物在支气管区域沉积的研究过程实际上是对支气管计算机和实体建模的日趋精细化、目的化以及选取更适合的计算条件和计算方法的过程。目前,对 1~5 级支气管的各种研究基本上确定了颗粒物沉积规律:① 随着呼吸流量的增大,2.5~10 μm 的颗粒物总沉积增大,且沉积趋向高级支气管迁移,小于 2.5 μm 的颗粒物受影响不大。② 各种模型均能模拟颗粒物在支气管区域的沉积分布,但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需要进一步验证。③ 入口流速分布、不同呼吸模式、呼吸流量函数对沉积作用有明显影响,但影响规律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统一。
3 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肺腺泡区沉积
根据人体肺生物力学模型[27],将 17 级以下的支气管和肺泡定义为肺腺泡区。人体肺腺泡区是呼吸作用的区域,研究此区域颗粒物沉降对于揭示颗粒物诱发疾病更具有参考价值,但也是目前研究的难点。目前研究主要以计算机仿真为主,模型包括单肺泡模型和多肺泡模型。
肺腺泡区目前仍不能通过 CT 技术建立真实的计算机模型,需进行大量的简化,如将肺腺泡简化为极细的圆柱形支气管等。但这些简化与实际情况差异过大,因此一些学者将肺泡单独分离出来构建单肺泡模型,进行局部沉积计算。Żywczyk 等[28]建立了单一肺泡模型,通过改变杨氏弹性模量分析颗粒物沉积率的变化,结果显示,杨氏弹性模量的增大引起了沉积率的增加,说明肺泡的生物力学特性对颗粒物沉积影响较为明显。Darquenne[29]、张鸿雁等[30]对单个肺泡进行模拟研究后认为,粒径小于 0.2 μm 的颗粒物主要沉积在肺泡区,肺泡内流场为稳定的层流流场,说明肺腺泡区颗粒物沉降主要是扩散引起的。Darquenne 等[31]研究还表明,采用可变体积的肺泡模型,由于肺泡体积变化将导致 1~5 μm 的颗粒物沉积减少。这些单肺泡模型成功之处在于获得了肺泡内流场状态,以较小的计算量获得颗粒物在肺泡沉积的基本规律。
由于单个肺泡与肺腺泡在形态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对于单个肺泡的研究并不能真实反映颗粒物的实际沉积行为。为了更进一步模拟人体肺腺泡的真实情况,Federspiel 等[32]首先建立了长对称轴围绕着环形小泡的肺腺泡模型,发现在固定肺泡壁模型下也存在流线分离和肺泡内的循环流,并进一步阐述了肺泡管的形状对颗粒沉积有重要的影响。Sznitman 等[33]通过建立可动肺泡壁三维模型对动态肺泡内流场特性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流场特性仅与肺泡所处级数有关的结论,并表明由肺泡壁运动诱发的肺泡内的对流现象对颗粒在肺腺泡内的沉积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更真实模拟肺泡内的颗粒沉积,Sznitman 等[34]建立了多级肺泡管的二维和三维模型来研究颗粒沉积,研究结果表明,重力对细颗粒的沉积有重要影响,同时发现各级肺泡管内颗粒的沉积具有不均匀性。Ma 等[35]建立了五级异面可动肺腺泡三维模型,研究了不同呼吸状态下气体流动特性、重力、多呼吸周期等因素对颗粒物沉积的影响,结果表明,可动肺泡壁和多呼吸周期对研究颗粒物精确沉积有重要影响。Khajeh-Hosseini-Dalasm 等[36]建立了多级腺泡模型探究腺泡级数对颗粒沉积的影响,发现一级模型不能精确模拟颗粒物在复杂、瞬变腺泡模型中的沉积情况。Oakes 等[37]建立了健康的和肺气肿的单簇肺泡计算机模型和粒子图像测速(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实验模型,将肺泡仿真与实验结合起来,结果发现颗粒物不能通过单次呼吸直接抵达肺泡壁,而是通过扩散作用沉积。由于 Oakes 采用的仍然是硬质模型,因此研究结果与 Darquenne 等[29]较为一致。
以上研究均对肺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简化,实体模型也采用了相似性原理以更接近实际呼吸情况。就整个肺部而言,肺泡的巨大数量以及大小结构的不同使得无法采用建模的方法完全模拟整个肺泡区的情况。以 Ma 等[35]建立的多级球形肺泡网络模型为例,体积仅仅为 187 mm3,是平均腺泡的 0.1%,因此最终限制了沉积结果向整个肺泡区域的扩展。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加努力构建真实肺泡模型,已有学者采用同步辐射 X 射线断层扫描显微镜(synchrotron radiation X-ray tomographic microscopy,SRXTM)技术重建了动物肺泡的真实模型[38]。但 SRXTM 在全世界应用很少,且目前只能重建冷冻小动物的肺(如老鼠),因此应用受到限制,近几年进展缓慢。另一种方法是采用组织工程法构建活体肺组织结构,但仍处于探索阶段[39]。相信随着新技术的进步,构建人体肺泡实体模型开展颗粒物沉积研究终将成为现实。
4 特殊情况下人体呼吸系统病态模型的可吸入颗粒物沉积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支气管阻塞、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会对肺形态学造成宏观上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可吸入颗粒物的沉积规律。Bahmanzadeh 等[4]研究了鼻腔阻塞性病变对呼吸气流存在明显影响,并进一步影响颗粒物在肺内的沉积。陈晓乐等[40]模拟了第 9 级支气管阻塞呼吸道内颗粒物的沉积,并发现变形使更多的颗粒在收缩处产生沉积,使原本阻塞的呼吸道愈发狭窄。Darquenne 等[41]研究认为肺阻塞患者在深呼吸时 1~2.9 μm 颗粒物沉积率高于健康受试者,这可能是肺阻塞患者呼吸频率快且肺内通风不均匀造成的。Wang 等[42]研究表明,肺泡前段支气管变窄后肺泡内沉积率明显降低。上述人体呼吸系统病态特征下的可吸入颗粒物沉积研究结果表明,支气管阻塞等条件下,可吸入颗粒物沉积规律与正常条件下不同。针对这些病态模型进行可吸入颗粒物的沉积研究能够进一步明确发病机理,为呼吸系统疾病预防和靶向药物治疗提供优化方案。
5 可吸入颗粒物沉积在肺部给药吸入治疗方面的应用研究
吸入性药物治疗是哮喘等肺部疾病的一线临床方法,沉积分布和沉积率决定了雾化吸入治疗的效果。Yang 等[43]总结发现,目前临床采用的雾化器肺部沉积率最高只能达到 35%,且沉积部位并不能完全满足靶向治疗的目的。采用计算机仿真或实体模型研究肺部沉积规律有助于研发更好的吸入设备、优化雾化药物制剂[44]。Feng 等[45]研究了呼吸道温度和颗粒物浓度分布,认为这些信息有助于呼吸道损伤和药物治疗的评估。研究表明,1~5 μm 颗粒物在不同呼吸条件下沉积率可相差 4 倍[46],因此选择合适的呼吸方式对于提高给药效率至关重要。Krafcik 等[47]模拟 100 nm 磁性药物颗粒在肺部的沉积情况,发现磁性环境能使颗粒物克服粘性阻力和重力影响,从而为增大肺泡内的药物沉积率提供了新思路。事实上,肺内沉积效率比体外测量有更多的可变因素,各参数相互关系的全面研究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挑战。
6 未来的研究重点
综上所述,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内沉积的研究逐渐从共性问题向特异性问题过渡,研究方法包括理论分析、数值计算、计算机模拟和实体模型实验等。通常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建立一个局部模型研究某一特定条件下颗粒物运动与沉积的规律,并与先前分析或计算模型比较,得出一致或不同的结论。但受限于模型和实验条件的真实性,这些研究在揭示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内真实沉积问题的意义有限。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的沉积情况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
(1)仿真与实验结果正确性验证。目前文献报道的仿真研究结果通常是与已发表的文献数据进行对比,无法与实际沉积结果进行比较。解决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可参照的标准实验动物模型,颗粒物采用可追踪的特殊粒子,再建立一系列仿真和实验模型,研究各模型之间结果的差异。
(2)局部沉积增强/降低方法的研究。这属于应用方面的研究,人体呼吸系统某一部位在临床上需要增强(如药物吸入治疗)或降低(如防止进一步病变)颗粒物沉积,需要采用仿真或实验模型,改变呼吸模式或颗粒物特性,达到局部沉积增强或降低的目的。
(3)生物颗粒物的沉积规律的研究。细菌、病毒、花粉等生物颗粒物表面特征复杂,且具有生物活性特征,因此研究生物颗粒物在呼吸系统内沉积规律,有助于揭示传染病传播、致病机理,探寻更有效的预防与治疗手段。
(4)湿度、温度的影响。呼吸过程是一个将空气加热和加湿的过程,以往的研究多忽略了这一过程,在未来的仿真和实验研究中,应重视温度、湿度对沉积作用的影响。
(5)呼吸系统生物学对沉积的影响。受限于计算机仿真的技术局限性,以往的研究无法充分考虑呼吸系统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如支气管和肺泡的粘弹性、粗糙度、呼吸道粘膜、纤毛等。而建立含有这些因素的仿真或实体实验模型,对于深入揭示可吸入颗粒物沉积规律具有更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应用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随着计算机建模技术、微断层扫描成像技术、生物力学、组织工程再生技术的进步,未来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中沉积规律的研究将逐步进入仿生、仿真化阶段,并针对疾病成因、发展、治疗等方面开展计算机仿真和实体实验模型的综合研究,并进一步走向临床应用。
引言
呼吸系统是空气中颗粒物进入人体的主要途径。颗粒物进入人体呼吸系统可能诱发肺癌、引起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带有致病微生物的颗粒物更是肺炎、结核、流感等各类传染病传播的主要方式。普遍认为,颗粒物直径越小,进入呼吸系统部位越深,超细颗粒物甚至能够穿透肺泡进入人体血液循环,从而导致心脑血管等相关疾病[1]。早在 1993 年,Dockery 等[2]对美国 6 个城市的 PM2.5 颗粒物(指平均粒径为 2.5 μm 的颗粒物)暴露健康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浓度每升高 10 μg/m3,心肺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均提高 18%。近年来的流行病学研究已证实,颗粒物浓度增加与呼吸系统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具有很强的相关性[3]。
大量解剖学和病理学研究表明,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的沉积部位与沉积量(一定时间内沉积在特定呼吸部位的颗粒物数量)[4]。因此,研究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沉积规律对于定量研究颗粒物的暴露风险及剂量健康效应至关重要。但由于采用志愿者只能获得呼吸系统总沉积率,而无法确定肺部各个部位的沉积差异,因此,国内外诸多学者采用模拟仿真法和实体实验模型法开展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介绍近年来人体鼻咽区、支气管区和肺腺泡区的模拟仿真和实验研究方法、结果,阐述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以指导可吸入颗粒物沉积模拟、实验和应用方面进一步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与指导价值。
1 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鼻咽区沉积
人体鼻咽区包括鼻腔和咽喉,是可吸入颗粒物首先进入人体的区域,由于结构复杂,内含粘膜和纤毛,对颗粒物随后进入气管和肺部的影响很大[5]。苏英锋等[6]对健康人鼻腔进行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成像后研究,发现气流在鼻腔内主要为层流,而上颌窦腔内气流则以自由扩散为主。Cisonni 等[7]构建人体鼻腔三维计算模型,研究虚拟钩突切除前后可吸入颗粒物的沉积情况,发现在进行了上颌窦手术后,患者通气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鼻窦区吸入纳米/微米级颗粒物的沉积明显增加。Xi 等[8]研究发现,人体喉部声门区的截面积变大将增大颗粒物在鼻咽区的沉积。以上研究表明,鼻咽部结构的变化明显影响此区域的可吸入颗粒物沉积。特别是增大呼吸截面积,可提高可吸入颗粒物在鼻咽区的沉积率。这对于预防可吸入颗粒物进一步在气管、支气管和肺腺泡区的沉积,提供了一种临床可操作的思路。黄小青等[9]研究了高速气流对人体鼻腔温度场影响,发现急促呼吸时鼻腔对呼吸温度场升温功能下降,从而影响整个呼吸系统的沉积。总之,鼻咽区是可吸入颗粒物进入人体呼吸系统的第一道屏障,其结构和呼吸方式对气管支气管的气流和颗粒物向肺部深处输送具有较大的影响。
2 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支气管沉积
支气管区域是目前人体呼吸系统中可吸入颗粒物沉积研究的焦点,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呼吸模式、颗粒物属性等对沉积率的影响,研究方法包括计算机仿真和实体实验模型等。
呼吸方式方面,Van Rhein等[10]研究了不同呼吸流量波形对沉积的影响,发现斜波、方波的沉积率比正弦波要高 43.65%,说明呼吸模式对可吸入颗粒物在支气管区沉降的重要影响。Sracic 等[11]研究了运动时 PM2.5 颗粒物的吸入沉积规律,发现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支气管区域总的沉积率随着运动强度而增加,说明剧烈运动时 PM2.5 沉积明显增大。Augusto 等[12]研究了睡眠、休息、适度的活动和激烈运动模式下粒径 1~3 μm 的颗粒物在前 4 级支气管内的沉积规律,发现不同模式下由重力引起的沉积之间差异最大可达 172%,布朗扩散沉积差异最大为 11%,进一步阐明呼吸模式影响沉积的本质是重力沉积影响。而在模拟条件方面,主要进行的是呼吸流量和颗粒物直径方面的影响研究。Islam 等[13]采用 CT 扫描技术建立上呼吸道数值计算模型,并对不同呼吸流量下颗粒物沉降的情况进行模拟研究,结论是流量越大沉降率越高,表明颗粒物沉积受支气管气流影响较为明显。
颗粒物特性方面,主要研究颗粒物形状、密度、大小、生物特性等。Rahimi-Gorji 等[14-15]研究表明,5~10 μm 颗粒物在呼吸流量为 30 L/min 时沉积率最高,而 1 μm 颗粒物则在 15 L/min 时最大,说明不同粒径的可吸入颗粒物受惯性碰撞影响不同。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呼吸流量增大,沉积向高级支气管迁移。Lintermann 等[16]研究表明,粒径 2.5~10 μm 的颗粒物仅有 0.69% 沉积在前 6 级支气管上,说明这一范围的颗粒物大部分进入到肺部更深处,可能带来更大的健康威胁。Darquenne 等[17]还研究了重力沉积效应对颗粒物沉积的影响,发现 0.5~3 μm 的颗粒物沉积率随密度增大而明显增大。而对于颗粒物本身通常需考虑其密度对沉积的影响,于申等[18]研究了不同密度的颗粒物沉积规律,发现随着密度的增大,颗粒物沉积率有所上升,且粒径越大,上升效果越明显。以上研究表明,重力是影响颗粒物在支气管区域沉积的重要因素。
目前,有学者对一些特殊颗粒物在支气管区域的沉积规律进行了研究。Dastan 等[19]研究了非圆形颗粒物在鼻腔中的沉积规律,认为颗粒物长径比应作为一个重要参数进行分析。Sturm[20]研究了纳米级超细颗粒物的运动轨迹以及沉积方式,研究表明纳米级颗粒物与微米级颗粒物的沉积形态包括沉积机理都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别,重力引起的惯性碰撞处于次要地位,主要沉积因素是扩散。因此在进行计算机仿真分析时,应根据所模拟的颗粒物直径选择相应的流体力学方程和算法。生物气溶胶颗粒物在形态学上更具有多样化特征,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生物颗粒物形状和呼吸条件对生物气溶胶沉积的影响最大[21],因此在研究生物气溶胶沉积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Winkler-Heil 等[22]研究了吸湿性颗粒物 NaCl 在人体呼吸系统的沉积。结果表明,由于呼吸系统的加湿作用,导致了 NaCl 吸水后重量和表面性质发生变化,从而降低了直径 0.1~0.7 μm 颗粒物的沉积率。这些研究充分表明,颗粒物形状、大小、表面特性以及生物学因素都会对其在呼吸系统内的沉积带来直接影响。
随着计算机建模技术的进步,研究者致力于建立更全面更接近真实的计算机模型。Kabilan 等[23]采用微计算机断层扫描(micron computed tomo- graphy,Micro-CT)成像技术,建立了 500 μm 级别的细末支气管模型,支气管出口达到 272 个。研究结果表明,粒径 1 μm 的颗粒物有 5.7% 沉积在支气管和细支气管。值得注意的是,Kabilan 等[23]还对建立的拥有 2 878 个支气管的大兔计算机模型进行分析,并与实体实验模型进行对比,发现计算机仿真结果与实体模型放射性实验结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该结果说明,即使建立的计算机仿真模型已相当接近真实,但与实际情况仍有较大差异。Islam 等[24]采用拓扑结构建立了包含 1 453 个支气管的复杂模型,是目前文献报道中支气管数目最多的计算机三维仿真模型,他们利用该模型研究了不同呼吸流量和颗粒物粒径对支气管沉积的影响,发现右肺支气管比左肺支气管沉积率更高,这可能是由于人体左右肺的结构差异造成的。
计算机仿真往往将可吸入颗粒物和人体呼吸系统进行理想化假设,因此仿真结果与实际情况之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差异。又由于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沉积后无法直接采样,放射成像法只能得到大致的数值,且放射剂量对人体具有潜在的健康威胁,因此尚未出现采用人体试验的方法研究呼吸系统的沉积效率。研究者们只有尝试通过构建体外实验模型来验证计算机仿真的结果。Borojeni 等[25]采用 CT 和三维(three dimension,3D)打印技术建立了成年人和儿童的 5 级支气管丙烯酸塑料实体模型,实验结果与以往发表过的经验模型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实验数据虽然具有较大的发散性,但整体趋势与理论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说明实体模型是研究可吸入颗粒物沉积的可行方法。李福生等[26]建立了包括口腔、悬雍垂、咽部、会厌、喉部、声门、梨状窝、气管和前 3 级支气管的实体模型,在模型内壁涂抹硅油模拟呼吸道壁面黏性,研究结果表明,粒径为 6.5 μm 的颗粒物在气管和前 3 级沉积率达 29%,而 Rahimi-Gorji 等[14]计算机仿真的结果为 19%,二者相差较大。由于目前实体模型方面的研究较少,尚无法得出其与计算机模型能否相互验证,或者哪一种方法更接近于真实的结论。
过去十余年,可吸入颗粒物在支气管区域沉积的研究过程实际上是对支气管计算机和实体建模的日趋精细化、目的化以及选取更适合的计算条件和计算方法的过程。目前,对 1~5 级支气管的各种研究基本上确定了颗粒物沉积规律:① 随着呼吸流量的增大,2.5~10 μm 的颗粒物总沉积增大,且沉积趋向高级支气管迁移,小于 2.5 μm 的颗粒物受影响不大。② 各种模型均能模拟颗粒物在支气管区域的沉积分布,但模拟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需要进一步验证。③ 入口流速分布、不同呼吸模式、呼吸流量函数对沉积作用有明显影响,但影响规律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统一。
3 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肺腺泡区沉积
根据人体肺生物力学模型[27],将 17 级以下的支气管和肺泡定义为肺腺泡区。人体肺腺泡区是呼吸作用的区域,研究此区域颗粒物沉降对于揭示颗粒物诱发疾病更具有参考价值,但也是目前研究的难点。目前研究主要以计算机仿真为主,模型包括单肺泡模型和多肺泡模型。
肺腺泡区目前仍不能通过 CT 技术建立真实的计算机模型,需进行大量的简化,如将肺腺泡简化为极细的圆柱形支气管等。但这些简化与实际情况差异过大,因此一些学者将肺泡单独分离出来构建单肺泡模型,进行局部沉积计算。Żywczyk 等[28]建立了单一肺泡模型,通过改变杨氏弹性模量分析颗粒物沉积率的变化,结果显示,杨氏弹性模量的增大引起了沉积率的增加,说明肺泡的生物力学特性对颗粒物沉积影响较为明显。Darquenne[29]、张鸿雁等[30]对单个肺泡进行模拟研究后认为,粒径小于 0.2 μm 的颗粒物主要沉积在肺泡区,肺泡内流场为稳定的层流流场,说明肺腺泡区颗粒物沉降主要是扩散引起的。Darquenne 等[31]研究还表明,采用可变体积的肺泡模型,由于肺泡体积变化将导致 1~5 μm 的颗粒物沉积减少。这些单肺泡模型成功之处在于获得了肺泡内流场状态,以较小的计算量获得颗粒物在肺泡沉积的基本规律。
由于单个肺泡与肺腺泡在形态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对于单个肺泡的研究并不能真实反映颗粒物的实际沉积行为。为了更进一步模拟人体肺腺泡的真实情况,Federspiel 等[32]首先建立了长对称轴围绕着环形小泡的肺腺泡模型,发现在固定肺泡壁模型下也存在流线分离和肺泡内的循环流,并进一步阐述了肺泡管的形状对颗粒沉积有重要的影响。Sznitman 等[33]通过建立可动肺泡壁三维模型对动态肺泡内流场特性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流场特性仅与肺泡所处级数有关的结论,并表明由肺泡壁运动诱发的肺泡内的对流现象对颗粒在肺腺泡内的沉积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更真实模拟肺泡内的颗粒沉积,Sznitman 等[34]建立了多级肺泡管的二维和三维模型来研究颗粒沉积,研究结果表明,重力对细颗粒的沉积有重要影响,同时发现各级肺泡管内颗粒的沉积具有不均匀性。Ma 等[35]建立了五级异面可动肺腺泡三维模型,研究了不同呼吸状态下气体流动特性、重力、多呼吸周期等因素对颗粒物沉积的影响,结果表明,可动肺泡壁和多呼吸周期对研究颗粒物精确沉积有重要影响。Khajeh-Hosseini-Dalasm 等[36]建立了多级腺泡模型探究腺泡级数对颗粒沉积的影响,发现一级模型不能精确模拟颗粒物在复杂、瞬变腺泡模型中的沉积情况。Oakes 等[37]建立了健康的和肺气肿的单簇肺泡计算机模型和粒子图像测速(particle image velocimetry,PIV)实验模型,将肺泡仿真与实验结合起来,结果发现颗粒物不能通过单次呼吸直接抵达肺泡壁,而是通过扩散作用沉积。由于 Oakes 采用的仍然是硬质模型,因此研究结果与 Darquenne 等[29]较为一致。
以上研究均对肺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简化,实体模型也采用了相似性原理以更接近实际呼吸情况。就整个肺部而言,肺泡的巨大数量以及大小结构的不同使得无法采用建模的方法完全模拟整个肺泡区的情况。以 Ma 等[35]建立的多级球形肺泡网络模型为例,体积仅仅为 187 mm3,是平均腺泡的 0.1%,因此最终限制了沉积结果向整个肺泡区域的扩展。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们更加努力构建真实肺泡模型,已有学者采用同步辐射 X 射线断层扫描显微镜(synchrotron radiation X-ray tomographic microscopy,SRXTM)技术重建了动物肺泡的真实模型[38]。但 SRXTM 在全世界应用很少,且目前只能重建冷冻小动物的肺(如老鼠),因此应用受到限制,近几年进展缓慢。另一种方法是采用组织工程法构建活体肺组织结构,但仍处于探索阶段[39]。相信随着新技术的进步,构建人体肺泡实体模型开展颗粒物沉积研究终将成为现实。
4 特殊情况下人体呼吸系统病态模型的可吸入颗粒物沉积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支气管阻塞、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会对肺形态学造成宏观上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可吸入颗粒物的沉积规律。Bahmanzadeh 等[4]研究了鼻腔阻塞性病变对呼吸气流存在明显影响,并进一步影响颗粒物在肺内的沉积。陈晓乐等[40]模拟了第 9 级支气管阻塞呼吸道内颗粒物的沉积,并发现变形使更多的颗粒在收缩处产生沉积,使原本阻塞的呼吸道愈发狭窄。Darquenne 等[41]研究认为肺阻塞患者在深呼吸时 1~2.9 μm 颗粒物沉积率高于健康受试者,这可能是肺阻塞患者呼吸频率快且肺内通风不均匀造成的。Wang 等[42]研究表明,肺泡前段支气管变窄后肺泡内沉积率明显降低。上述人体呼吸系统病态特征下的可吸入颗粒物沉积研究结果表明,支气管阻塞等条件下,可吸入颗粒物沉积规律与正常条件下不同。针对这些病态模型进行可吸入颗粒物的沉积研究能够进一步明确发病机理,为呼吸系统疾病预防和靶向药物治疗提供优化方案。
5 可吸入颗粒物沉积在肺部给药吸入治疗方面的应用研究
吸入性药物治疗是哮喘等肺部疾病的一线临床方法,沉积分布和沉积率决定了雾化吸入治疗的效果。Yang 等[43]总结发现,目前临床采用的雾化器肺部沉积率最高只能达到 35%,且沉积部位并不能完全满足靶向治疗的目的。采用计算机仿真或实体模型研究肺部沉积规律有助于研发更好的吸入设备、优化雾化药物制剂[44]。Feng 等[45]研究了呼吸道温度和颗粒物浓度分布,认为这些信息有助于呼吸道损伤和药物治疗的评估。研究表明,1~5 μm 颗粒物在不同呼吸条件下沉积率可相差 4 倍[46],因此选择合适的呼吸方式对于提高给药效率至关重要。Krafcik 等[47]模拟 100 nm 磁性药物颗粒在肺部的沉积情况,发现磁性环境能使颗粒物克服粘性阻力和重力影响,从而为增大肺泡内的药物沉积率提供了新思路。事实上,肺内沉积效率比体外测量有更多的可变因素,各参数相互关系的全面研究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挑战。
6 未来的研究重点
综上所述,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内沉积的研究逐渐从共性问题向特异性问题过渡,研究方法包括理论分析、数值计算、计算机模拟和实体模型实验等。通常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建立一个局部模型研究某一特定条件下颗粒物运动与沉积的规律,并与先前分析或计算模型比较,得出一致或不同的结论。但受限于模型和实验条件的真实性,这些研究在揭示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内真实沉积问题的意义有限。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的沉积情况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
(1)仿真与实验结果正确性验证。目前文献报道的仿真研究结果通常是与已发表的文献数据进行对比,无法与实际沉积结果进行比较。解决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可参照的标准实验动物模型,颗粒物采用可追踪的特殊粒子,再建立一系列仿真和实验模型,研究各模型之间结果的差异。
(2)局部沉积增强/降低方法的研究。这属于应用方面的研究,人体呼吸系统某一部位在临床上需要增强(如药物吸入治疗)或降低(如防止进一步病变)颗粒物沉积,需要采用仿真或实验模型,改变呼吸模式或颗粒物特性,达到局部沉积增强或降低的目的。
(3)生物颗粒物的沉积规律的研究。细菌、病毒、花粉等生物颗粒物表面特征复杂,且具有生物活性特征,因此研究生物颗粒物在呼吸系统内沉积规律,有助于揭示传染病传播、致病机理,探寻更有效的预防与治疗手段。
(4)湿度、温度的影响。呼吸过程是一个将空气加热和加湿的过程,以往的研究多忽略了这一过程,在未来的仿真和实验研究中,应重视温度、湿度对沉积作用的影响。
(5)呼吸系统生物学对沉积的影响。受限于计算机仿真的技术局限性,以往的研究无法充分考虑呼吸系统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如支气管和肺泡的粘弹性、粗糙度、呼吸道粘膜、纤毛等。而建立含有这些因素的仿真或实体实验模型,对于深入揭示可吸入颗粒物沉积规律具有更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应用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随着计算机建模技术、微断层扫描成像技术、生物力学、组织工程再生技术的进步,未来可吸入颗粒物在人体呼吸系统中沉积规律的研究将逐步进入仿生、仿真化阶段,并针对疾病成因、发展、治疗等方面开展计算机仿真和实体实验模型的综合研究,并进一步走向临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