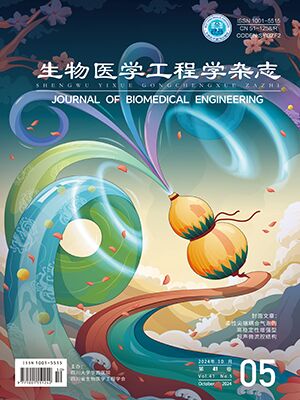本文旨在研究持续短阵快速脉冲刺激(cTBS)干预对情绪加工脑功能网络的影响。我们采用 cTBS 技术对 10 名受试者的左前额背外侧皮质(DLPFC)区域进行干预,同时记录干预前后受试者进行情绪面孔性别识别任务时的头皮脑电(EEG)信号,然后采用 EEG 信号相位同步值来衡量两个脑网络节点间的连接强度,并运用网络效率来描述脑区的信息传递效率。研究结果发现,经由 cTBS 技术干预受试者脑区,再采用情绪面孔图片刺激后,100~300 ms 时间窗内的 EEG 信号的 β 频段的事件相关功率明显增强;不同的情绪图片刺激下,中性和负性情绪图片刺激的 EEG 信号全局相位同步值比正性情绪刺激下更高;情绪加工脑网络小世界特性增强。综上所述,本文通过研究左侧 DLPFC 活跃性改变对情绪加工脑网络的影响,初步探索了情绪加工脑网络机制,为以后的情绪加工脑网络研究提供了参考。
引用本文: 李琦, 曹丹, 李颖洁, 唐莺莹. 持续短阵快速脉冲刺激对情绪加工脑网络影响的研究. 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 2017, 34(4): 518-528. doi: 10.7507/1001-5515.201606048 复制
引言
人类的情绪加工是一个多层次结构相互作用的脑功能网络活动[1],而大量研究表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2-3]。例如,很多基于神经影像学的研究发现,在情绪识别任务下,DLPFC 的活动增加[4-5];与中性和正性情绪识别任务相比,右侧 DLPFC 的活动与负性情绪的识别任务相关度更高[6];还有学者发现与正常人相比,轻度抑郁症患者做情绪性别识别任务尤其是在负性情绪刺激下的性别识别任务时,左侧 DLPFC 活跃性降低[7]。但是,这些研究还局限在特定脑区发生的特异性改变,而 DLPFC 与其他脑区的功能连接性是了解情绪加工网络的基础[8],因此 DLPFC 活跃性的变化对情绪加工时的脑功能网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Koelsch 等[9]采用静息状态的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数据,使用特征中心向量和功能连接分析方法揭示了在快乐的情绪面孔刺激下的脑功能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Zhang 等[10]采用静息状态的 fMRI 数据,使用图论方法分析得出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静息状态下的大脑网络都具有小世界特性,但是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功能网络更倾向于随机化。在相关研究中,除了采用 fMRI 数据构建脑功能网络的研究,由于情绪认知过程中大脑活动的变化是毫秒级别的,使得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 EEG 信号也成为常用的一种研究手段。Lee 等[11]采用 EEG 信号分类不同的情绪状态的研究发现,正常受试者的前额区在负性情绪状态下的相位同步指数低于正性情绪状态,并且指出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大脑连通性会发生变化。Mar-tini 等[12]采用 EEG 信号基于 γ 频段相位同步研究发现在不快乐情绪刺激下大脑颞区和额区的功能连接紧密。另外,本小组 Li 等[13]在前期基于情绪加工任务下 EEG 信号的研究中,采用相干的方法构建脑功能网络,发现无论是抑郁症患者还是正常对照组其 γ 频段下面孔情绪加工的脑功能网络都是规则网络。但是,仅凭 fMRI 图像或 EEG 信号的研究结果都无法直接证明特定的脑区在情绪加工网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技术通过调节大脑皮层神经元的膜电位激活大脑,可无创伤地改变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具有形成“虚拟损伤”等特性[14],是一种能有效研究特定脑区在网络中的作用的技术,对于研究活体人脑功能的因果关系有其他技术无可替代的优势。因而,TMS 技术结合 EEG 信号的研究方法成为脑网络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15],可以很好地用来研究特定脑区在脑功能网络中的活动特性。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采用相位同步法来描述高分辨率的 EEG 数据各通道之间的连通性,然后运用特定频段建立大脑网络模型,分析网络的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最终得出 TMS 干预左侧 DLPFC 前后情绪加工脑网络的差异性,从而探究左侧 DLPFC 活跃程度的变化对情绪加工脑网络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情绪加工脑网络机制,为以后的情加工脑网络研究提供了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试验共选取受试者 10 人,皆为上海大学学生,其中男性 7 人,女性 3 人,年龄(24.3±0.9)岁,受教育年限(17.1±0.7)年。所有受试者均右利手,视力正常或者矫正正常,无神经损伤史,无家族遗传病史,无药物和酒精滥用史。试验前,所有受试者需完成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并填写 TMS 和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检查安全筛查问卷。经证实,所选受试者都符合试验条件,各量表评分均在正常范围内,SAS 标准评分为 35.75±10.5,SDS 标准分评分为 31.75±11.5,HAMD 标准分评分为 7.27±6.9。所有受试者在试验前均自愿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试验结束后给予了适量的报酬。所有试验方案通过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
1.2 试验方法
本试验让受试者进行情绪面孔的性别识别任务,整个试验过程设计如图 1 所示。试验分为两部分,每部分时间间隔一周。第一部分采集 2 min 静息 EEG 信号后,开始情绪面孔性别识别任务;第二部分试验开始前先测量静息运动阈值(rest motor threshold,RMT),具体测量方法如图 1 所示。接着再结合 MRI 导航(即借助于 MRI 成像,获取和更新介入器械的三维方位信息,然后对 MRI 图像和介入器械的信息进行标定后,经过图像融合可以共同显示在一个三维操作界面实现导航)进行持续短阵快速脉冲刺激(continuous theta-burst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cTBS)干预,然后重复第一部分的试验内容,最后再次测量 RMT。
 图1
试验流程图
Figure1.
Flow chart of the experiment
图1
试验流程图
Figure1.
Flow chart of the experiment
试验选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中的中国人真实面孔图片(正性,负性和中性各 24 张,均为 12 男 12 女)作为情绪刺激材料,且均为黑白照片,大小相同,无明显标志。试验过程中,受试者要求做一个情绪面孔性别识别任务。试验程序由美国 PST(Psychology software tools)公司的 E-Prime 2.0 软件编写。每个刺激序列包含 400~600 ms 的随机间隔[以符号(+)显示]、1 000 ms 的面孔图片和 1 500 ms 的性别判定框,整个刺激序列的呈现流程如图 2 所示。图片随机呈现,判定框紧随在面孔图片后,框中出现“男?”或“女?”,要求受试者对面孔图片的性别做出及时地判断,若判定框中呈现的文字与面孔图片的性别一致,按键“1”;若不一致,按键“2”。整个试验分为 4 组,每组包含 72 个序列,正性、中性和负性图片各 24 张。做完一组试验后,受试者休息 1 min,整个试验任务大约耗时 20 min。
 图2
刺激序列示意图
Figure2.
Schematic diagram of stimulation sequence
图2
刺激序列示意图
Figure2.
Schematic diagram of stimulation sequence
1.3 TMS 试验
cTBS 是一种特殊的 TMS 技术,具有干预时间短、皮层受抑制时间长的特点[16]。本试验采用最大输出强度为 2.5 T 的 MedtronicMagPro X100 刺激仪(磁头型号为 MCF-B65,丹麦)对受试者的左侧 DLPFC 进行 cTBS 干预。cTBS 模式设置为每 200 ms 释放 3 串 50 Hz 的脉冲,共刺激 40 s。运动阈值的测定刺激线圈位于左侧运动皮层处(国际 10–20 系统的 FC3 附近)。记录电极位于右手拇指展肌肌腹位置,参考电极位于拇指第二关节处,接地电极位于手背处。刺激时线圈紧贴头皮并与头皮相切,受试者肌肉处于放松状态。刺激强度由 45% 递增或递减。在某一个刺激强度的 10 次连续刺激中,如果有 5 次引出波幅在 50 μV 以上的运动诱发电位,则认为该刺激强度是 RMT,它反映了中枢运动神经的兴奋性。本试验采用 90%RMT 的强度进行干预。试验时借助了 MRI 的导航定位,精确地把握干预位置。
1.4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试验数据采集设备为 64 导高密度 EEG 信号检测仪(BrainCap 标准型,德国),导联方法采用国际 10–20 系统,记录软件采用 Brain Products 公司研发的 Vision Recorder 系统;数据预处理采用 Vision Analyzer 系统。由于采集过程中 FP1、FP2、TP9、TP10 电极阻抗过大,所以试验数据分析中选用了 58 个电极位置,EEG 信号采样频率为 1 000 Hz,电极和头皮接触电阻小于 20 kΩ。预处理步骤包括带通滤波(0.05~80 Hz)、邻近导联平均(去掉不好的导联)、去眼电信号干扰、数据分段(刺激前 200 ms 到刺激后 1 000 ms 为一段)、基线校正(前 200 ms 数据视为基线)、伪迹校正(剔除大于 100 μV 的数据段)等,最后将数据导出作后续处理。
考虑到数据的鲁棒性和合理性[17],本文在后续处理中选取刺激后 800 ms 的 EEG 数据作为原始数据。首先进行事件相关功率谱分析,选取相应的频段。然后为了探索 cTBS 刺激下的大脑情绪加工的时变信息,本研究将数据进行分窗处理,从刺激时刻开始每 200 ms 取一个窗,以 50 ms 为步长选取第二个窗,即 1~200 ms 为第一个窗,50~250 ms 为第二个窗,依此类推直到包含全部数据,共 13 个窗。因此,刺激后 800 ms 的数据共分成 13 个数据段。试验获取相应频段的数据采用小波分解方法,将预处理后的 EEG 信号分为 δ(1~4 Hz),θ(4~8 Hz),α(8~12 Hz),β(12~30 Hz),低 γ(30~50 Hz),高 γ(50~80 Hz)6 个频段,选取 db5 作为“母小波”,分解级数为 7。
1.5 事件相关功率谱分析
研究证实,运动、感知和认知的信息加工,会引起 EEG 信号的变化,形成事件相关去同步化(event-related desynchronization,ERD)和同步化(event-related synchronization,ERS),通过事件相关功率谱(event-related spectral perturbation,ERSP)可以衡量 ERD/ERS 的变化[18]。本文使用 db5 小波的复指数形式计算谱功率。
定义小波的复指数的解析式为:

 ,式中
,式中
 代表窗函数。则信号
代表窗函数。则信号
 的时频分析定义为:
的时频分析定义为:
 |
f 和 t 分别代表频率和时间。
对每段 EEG 数据进行小波变换,对变换后的所有数据段进行平均后取绝对值,即定义为平均 ERSP:
 |
最后,本研究对平均 ERSP 做基线矫正,即通过逐点减去前 200 ms 的 ERSP,得到相对基线的 ERSP。
1.6 脑功能网络分析
基于 EEG 信号研究特定频带内的脑网络时,采用相位同步来量化各通道信号之间的关系比较合适[19]。脑功能分析的第一步是构建网络,本文采用相位同步法构建基于多通道 EEG 信号的大脑网络。它是通过希尔伯特(Hilbert)变换把窄带的波形信号分解成幅度部分和相位部分,进而分析两信号间的相位关系[14]。如对于 EEG 信号采集电极 A 和 B,若解析信号的相位差满足:
 |
那么就称两信号相位同步(通常取 p=q=1)。信号间的相位同步水平可以用相位同步指数来刻画,定义相位同步指数为 r,如式(4)所示。
 |
其中,M 为采样点数。则 r 值在[0,1]之间,值为 1 表示相位完全同步;值为 0 表示相位完全不同步,代表了网络的连接强度。最终可以得到 58×58 的矩阵。
在确定网络连接强度之后,计算网络成本。网络成本(Cost)也就是网络的密度,即网络的连接边数与最大可能连接边数的比,如式(5)所示。式中,N 代表网络中节点(EEG 通道)总数,K 代表网络中存在的连接边数。
 |
本研究选取网络成本范围为[0.02,0.5][20],步长为 0.02,在每一个确定的网络成本下根据公式(5)计算 K 值,由 K 值确定阈值(连接强度),对相位同步矩阵转化为加权无向网络,即仅当矩阵中元素大于等于阈值时保留相应的值,否则为 0。在每个网络成本下建立加权网络后,计算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值。另外本文在建立每个加权网络的同时构建相应的随机网络和规则网络,该随机网络和规则网络具有与真实网络相同的节点数和有效连接边(N=58,K 是不同密度下有效连接边数),并计算其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值。本文构建网络借助 MATLAB 2011BCT 工具包中的功能函数对构建网络进行分析。网络分析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3
基于 EEG 信号的脑功能网络分析流程
Figure3.
Analysis process of brain function network based on EEG signals
图3
基于 EEG 信号的脑功能网络分析流程
Figure3.
Analysis process of brain function network based on EEG signals
1.7 网络效率分析
在网络的连通图中,Li,j 定义为最短路径长度即连接 i 节点和 j 节点的所有路径中,连接边数的最小值。两节点之间的连接效率与最短路径长度成反比。网络的全局效率 Eglobal,代表了整个网络的信息交换能力,定义为
 |
全局效率值越大,表示信息或能量等在该网络上进行交换时所需的代价越小[19]。
局部效率近似于聚类系数,反映了对一个特定节点 i 的最邻近间信息交换能力。定义局部效率 Elocal 为:
 |
式中,NGi 表示子网络 Gi 中节点的个数。平均局部效率是子网络中每个节点效率的平均值。网络的成本效率为网络的全局效率与网络的成本之差。
 |
网络的成本效率随着网络的改变而改变。
本文在分析单一网络成本下的局部特征时,又将大脑划分为左、右半球两个脑区和左/右额区,左/右颞区,左/右顶区和左/右枕区八个脑区。每个脑区的所有电极的局部效率均值作为该区域的局部效率值。如图 4 所示,中线左边为左半球,从上到下,从左至右分别是左额/颞/顶/枕,中线右边则为相应的右半球脑区。对不同情绪下的局部效率值做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组间因数为 cTBS(干预前/干预后)、半球(左/右)和脑区(额/颞/顶/枕)。
 图4
各个脑区选取分布图
Figure4.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brain regions selected
图4
各个脑区选取分布图
Figure4.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brain regions selected
1.8 统计分析
本试验数据都通过 SPSS 16.0 中的一般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GLM)完成统计分析。对各项统计检测值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内因素为情绪(正性/负性/中性)和 cTBS 干预(干预前/干预后),无组间因素。若 cTBS 与情绪之间(cTBS & 情绪)存在交互效应,则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对于统计分析结果的描述,如果检验 P<0.05,则认为存在主效应或交互效应。
2 结果
2.1 事件相关功率谱
如图 5 所示,为包括 cTBS 干预前和干预后,以及正、中、负性三种情绪刺激在内的 ERSP 时频图。可以看出:在情绪加工过程中,频带在 40 Hz 以内出现活跃状态,并且在 β 频带内 100~300 ms 脑内活动明显增强;然而,cTBS 干预后抑制了大脑的活动,脑内能量明显降低,尤其是负性情绪的变化非常明显。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 100~300 ms 内 β 频段内的大脑网络特性。
 图5
cTBS 干预前后三种情绪刺激下 ERSP 图
Figure5.
ERSP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under three kinds of emotional stimuli
图5
cTBS 干预前后三种情绪刺激下 ERSP 图
Figure5.
ERSP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under three kinds of emotional stimuli
2.2 情绪加工网络
本文采用相位同步法量化 EEG 通道间的关系,建立多网络密度下的情绪加工脑功能网络,进而进行复杂网络分析。如图 6 所示为 cTBS 干预前/后,三种情绪刺激下 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的相位同步矩阵。其中矩阵大小 58×58,每个元素表示相位同步指数,对角线元素为 0。横、纵坐标代表相应的导联,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对应的是大脑从前到后的导联分布。
 图6
β 频段 100~300 ms 时间窗的相位同步矩阵
Figure6.
100~300 ms Phase synchronization matrix of β band
图6
β 频段 100~300 ms 时间窗的相位同步矩阵
Figure6.
100~300 ms Phase synchronization matrix of β band
对 β 频段在 100~300 ms 内的全局相位同步值统计分析发现,cTBS 存在主效应趋势(F=4.529,P=0.062)以及 cTBS 与情绪之间存在着交互效应趋势(F=3.438,P=0.059)。又通过进一步地简单效应分析得到:① cTBS 干预前三种情绪两两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TBS 干预后,正性情绪与中性情绪(F=7.984,P=0.020)以及与负性情绪(F=6.222,P=0.034)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 中性情绪刺激下 cTBS 干预后相位同步值增加(F=7.918,P=0.020);负性情绪刺激下 cTBS 干预后相位同步值具有增加的趋势(F=3.411,P=0.098);而正性情绪刺激下 cTBS 干预前后的全局相位同步值无明显差异,如图 7 所示。
 图7
cTBS 干预前后 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平均全局相位同步值 *P<0.05
Figure7.
100~300 ms Phase synchronization average value of β band under the positive,neutral or negative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P<0.05
图7
cTBS 干预前后 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平均全局相位同步值 *P<0.05
Figure7.
100~300 ms Phase synchronization average value of β band under the positive,neutral or negative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P<0.05
试验中,将基于 EEG 信号构建的情绪加工网络与相应的随机网络和规则网络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情绪加工网络在网络密度(0.24,0.5)内,全局效率低于随机网络而高于规则网络,其局部效率则高于随机网络而低于规则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随网络密度变化的曲线如图 8 所示,第一列为正性、中性和负性三种情绪加工网络的全局效率曲线,第二列为对应的局部网络曲线。我们再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局部效率在密度(0.24,0.36)下都有 cTBS 主效应或主效应趋势,全局效率在(0.24,0.5)区间内无任何差异。另外,没有情绪主效应或 cTBS 与情绪之间的交互效应存在。由小世界网络特性可知,网络密度在(0.24,0.36)内,cTBS 干预后情绪加工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增强,如表 1 所示。
 图8
随机和规则网络及 cTBS 干预前后的情绪加工网络的全局和局部效率曲线图
Figure8.
Global and local efficiency curve of random,lattice or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ing of emotion
图8
随机和规则网络及 cTBS 干预前后的情绪加工网络的全局和局部效率曲线图
Figure8.
Global and local efficiency curve of random,lattice or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ing of emotion
2.3 单一网络密度下的网络局部特征
网络密度也即是网络的成本,网络的成本效率可以说明是全局网络与成本的差。β 频段 100~300 ms 时间窗内各因数下的成本-效率的关系如图 9 所示,可以看出,成本效率在较低成本区间内逐渐增大,达到一个最大值,然后成下降趋势,整个曲线犹如抛物线。cTBS 干预前、后,正、中、负性三种情绪加工网络的最大成本效率对应的成本在 0.28 左右。此时,网络具有最“经济”的模式。
 图9
cTBS 干预前后,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成本效率曲线图
Figure9.
Cost efficiency curve of the 100~300 ms time window of β band in three kinds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图9
cTBS 干预前后,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成本效率曲线图
Figure9.
Cost efficiency curve of the 100~300 ms time window of β band in three kinds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针对最“经济”模式下(网络密度 0.28)的脑网络,我们进一步选择了对大脑区域的局部效率进行分析。局部效率的脑地形图如图 10 所示。在 100~300 ms 时间窗内,正性情绪刺激下,干预后各个脑区的局部效率值高于干预前。中性情绪刺激下,干预后左半球各个脑区的局部效率值都高于干预前,右半球脑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且在 cTBS 干预后,左额、左颞、左顶区的局部效率值都高于右侧对应的脑区,枕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负性情绪刺激下,同样显示左半球各个脑区干预后的局部效率值高于干预前,干预后左半球的局部效率值高于右半球。
 图10
cTBS 干预前后 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局部效率的脑地形图
Figure10.
Brain topographic map of the local efficiency of the 100~300 ms time window of β band in three kinds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图10
cTBS 干预前后 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局部效率的脑地形图
Figure10.
Brain topographic map of the local efficiency of the 100~300 ms time window of β band in three kinds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3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 cTBS 干预下 EEG 信号特性,探究左侧 DLPFC 在情绪加工脑网络的作用。结果表明,ERSP 在 cTBS 干预后 100~300 ms 与干预前相比出现增强,尤其是 β 频带范围内激活明显。干预后,正性情绪刺激下的 EEG 信号全局相位同步值和中性、负性情绪刺激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一定的网络成本范围内,情绪加工网络的全局效率及局部效率介于随机网络和规则网络之间,具有小世界特性,而且,在网络成本区间(0.24,0.36)内,cTBS 干预后,脑功能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增强。
很多研究都已经表明,大脑前额在情绪加工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作用[2-3]。神经影像学的研究表明左侧 DLPFC 涉及到负性情绪的判别[6]。如前所述,有研究者发现与正常人相比,轻度抑郁症患者做情绪性别识别任务尤其是在负性情绪刺激下的情绪性别识别任务时,左侧 DLPFC 活跃性降低[7]。本试验通过采用 cTBS 技术抑制左侧 DLPFC 的活动后,发现相比于正性和中性情绪刺激,负性情绪刺激下情绪面孔性别识别任务的 ERSP 降低更明显。进一步证明了左侧 DLPFC 在负性情绪判别中的特殊作用。
EEG 信号相位同步值分析结果显示,cTBS 干预后与干预前相比,情绪加工脑网络具有高的全局相位同步值。研究发现大脑信息整合和处理的潜在机制是各神经网络的同步性震荡引起的,部分难以治愈的神经性疾病由大脑整体和局部整合过程的不足和异常造成[21]。而 EEG 信号反映的是神经元集群突触后电位的累积效应,其相位同步能反应大脑神经电活动的整合作用,高的相位同步可能对应着大脑大范围的整合[22],代表大脑具有很高的信息整合能力。另外,研究证明 DLPFC 与其他区域的紧密连接以及皮下层区域间的非直接联系参与了情绪认知信息加工,侧前额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LPFC)更涉及到高阶的认知处理[23]。本研究中 DLPFC 的活动受到抑制,打乱了原有的功能连接,为了完成情绪面孔性别识别任务,必须重新调动和整合各参与脑区的资源,最终导致网络的全局相位同步值升高。
很多研究者证实了人脑网络存在着小世界特性[20],并指出小世界网络具有较小的特征路径长度和较大的聚类系数。基于解剖学的研究也发现了大脑具有短的轴突连接或者低的代谢消耗,即大脑可以选择在某些范围内紧密连接,达到较为高效的“经济”模式,以降低能量消耗[24]。这意味着大脑具有更高的全局和局部效率。本研究中,使用网络成本系列值计算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值,得到情绪加工网络小世界特性区间为(0.24,0.5)。已有研究利用神经影像技术数据建立大脑网络,证明功能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在中低成本区间内[25-26]。cTBS 干预左侧 DLPFC,抑制了该区域大脑的活动,可能同时促进了对侧区域的皮层兴奋[27-28]。因此,干预后特定局域内功能网络发生改变,使得局部范围的连接更紧密,从而具有较高的局部效率。
当网络的成本效率达到峰值,如图 9 所示,即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高的效率时,此时“经济”的小世界网络特性体现最为明显。本研究中,网络成本为 0.28 时,成本效率达到峰值,表明此时的网络最“经济”。当网络成本效率达到最大时,我们发现干预后的左半球局部效率有所增加,这可能与干预后引起局部范围的连接紧密有关。
本研究揭示了 cTBS 干预后情绪加工网络小世界特性增强,证明了当成本效率在中低范围内,具有特异的网络性质,证明了左侧 DLPFC 活跃性改变对情绪加工脑网络的影响。本文的试验是对情绪加工网络机制的初步探索,为以后的情绪脑功能网络研究提供了参考,未来的工作应从网络分析方法中多个角度更全面地分析情绪脑功能网络特征,进一步研究情绪加工网络机制。
引言
人类的情绪加工是一个多层次结构相互作用的脑功能网络活动[1],而大量研究表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2-3]。例如,很多基于神经影像学的研究发现,在情绪识别任务下,DLPFC 的活动增加[4-5];与中性和正性情绪识别任务相比,右侧 DLPFC 的活动与负性情绪的识别任务相关度更高[6];还有学者发现与正常人相比,轻度抑郁症患者做情绪性别识别任务尤其是在负性情绪刺激下的性别识别任务时,左侧 DLPFC 活跃性降低[7]。但是,这些研究还局限在特定脑区发生的特异性改变,而 DLPFC 与其他脑区的功能连接性是了解情绪加工网络的基础[8],因此 DLPFC 活跃性的变化对情绪加工时的脑功能网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Koelsch 等[9]采用静息状态的功能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数据,使用特征中心向量和功能连接分析方法揭示了在快乐的情绪面孔刺激下的脑功能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Zhang 等[10]采用静息状态的 fMRI 数据,使用图论方法分析得出抑郁症患者和正常人静息状态下的大脑网络都具有小世界特性,但是抑郁症患者的大脑功能网络更倾向于随机化。在相关研究中,除了采用 fMRI 数据构建脑功能网络的研究,由于情绪认知过程中大脑活动的变化是毫秒级别的,使得具有高时间分辨率的 EEG 信号也成为常用的一种研究手段。Lee 等[11]采用 EEG 信号分类不同的情绪状态的研究发现,正常受试者的前额区在负性情绪状态下的相位同步指数低于正性情绪状态,并且指出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大脑连通性会发生变化。Mar-tini 等[12]采用 EEG 信号基于 γ 频段相位同步研究发现在不快乐情绪刺激下大脑颞区和额区的功能连接紧密。另外,本小组 Li 等[13]在前期基于情绪加工任务下 EEG 信号的研究中,采用相干的方法构建脑功能网络,发现无论是抑郁症患者还是正常对照组其 γ 频段下面孔情绪加工的脑功能网络都是规则网络。但是,仅凭 fMRI 图像或 EEG 信号的研究结果都无法直接证明特定的脑区在情绪加工网络中的作用。另一方面,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技术通过调节大脑皮层神经元的膜电位激活大脑,可无创伤地改变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具有形成“虚拟损伤”等特性[14],是一种能有效研究特定脑区在网络中的作用的技术,对于研究活体人脑功能的因果关系有其他技术无可替代的优势。因而,TMS 技术结合 EEG 信号的研究方法成为脑网络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15],可以很好地用来研究特定脑区在脑功能网络中的活动特性。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采用相位同步法来描述高分辨率的 EEG 数据各通道之间的连通性,然后运用特定频段建立大脑网络模型,分析网络的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最终得出 TMS 干预左侧 DLPFC 前后情绪加工脑网络的差异性,从而探究左侧 DLPFC 活跃程度的变化对情绪加工脑网络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情绪加工脑网络机制,为以后的情加工脑网络研究提供了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试验共选取受试者 10 人,皆为上海大学学生,其中男性 7 人,女性 3 人,年龄(24.3±0.9)岁,受教育年限(17.1±0.7)年。所有受试者均右利手,视力正常或者矫正正常,无神经损伤史,无家族遗传病史,无药物和酒精滥用史。试验前,所有受试者需完成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并填写 TMS 和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检查安全筛查问卷。经证实,所选受试者都符合试验条件,各量表评分均在正常范围内,SAS 标准评分为 35.75±10.5,SDS 标准分评分为 31.75±11.5,HAMD 标准分评分为 7.27±6.9。所有受试者在试验前均自愿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试验结束后给予了适量的报酬。所有试验方案通过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
1.2 试验方法
本试验让受试者进行情绪面孔的性别识别任务,整个试验过程设计如图 1 所示。试验分为两部分,每部分时间间隔一周。第一部分采集 2 min 静息 EEG 信号后,开始情绪面孔性别识别任务;第二部分试验开始前先测量静息运动阈值(rest motor threshold,RMT),具体测量方法如图 1 所示。接着再结合 MRI 导航(即借助于 MRI 成像,获取和更新介入器械的三维方位信息,然后对 MRI 图像和介入器械的信息进行标定后,经过图像融合可以共同显示在一个三维操作界面实现导航)进行持续短阵快速脉冲刺激(continuous theta-burst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cTBS)干预,然后重复第一部分的试验内容,最后再次测量 RMT。
 图1
试验流程图
Figure1.
Flow chart of the experiment
图1
试验流程图
Figure1.
Flow chart of the experiment
试验选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化面孔情绪图片系统中的中国人真实面孔图片(正性,负性和中性各 24 张,均为 12 男 12 女)作为情绪刺激材料,且均为黑白照片,大小相同,无明显标志。试验过程中,受试者要求做一个情绪面孔性别识别任务。试验程序由美国 PST(Psychology software tools)公司的 E-Prime 2.0 软件编写。每个刺激序列包含 400~600 ms 的随机间隔[以符号(+)显示]、1 000 ms 的面孔图片和 1 500 ms 的性别判定框,整个刺激序列的呈现流程如图 2 所示。图片随机呈现,判定框紧随在面孔图片后,框中出现“男?”或“女?”,要求受试者对面孔图片的性别做出及时地判断,若判定框中呈现的文字与面孔图片的性别一致,按键“1”;若不一致,按键“2”。整个试验分为 4 组,每组包含 72 个序列,正性、中性和负性图片各 24 张。做完一组试验后,受试者休息 1 min,整个试验任务大约耗时 20 min。
 图2
刺激序列示意图
Figure2.
Schematic diagram of stimulation sequence
图2
刺激序列示意图
Figure2.
Schematic diagram of stimulation sequence
1.3 TMS 试验
cTBS 是一种特殊的 TMS 技术,具有干预时间短、皮层受抑制时间长的特点[16]。本试验采用最大输出强度为 2.5 T 的 MedtronicMagPro X100 刺激仪(磁头型号为 MCF-B65,丹麦)对受试者的左侧 DLPFC 进行 cTBS 干预。cTBS 模式设置为每 200 ms 释放 3 串 50 Hz 的脉冲,共刺激 40 s。运动阈值的测定刺激线圈位于左侧运动皮层处(国际 10–20 系统的 FC3 附近)。记录电极位于右手拇指展肌肌腹位置,参考电极位于拇指第二关节处,接地电极位于手背处。刺激时线圈紧贴头皮并与头皮相切,受试者肌肉处于放松状态。刺激强度由 45% 递增或递减。在某一个刺激强度的 10 次连续刺激中,如果有 5 次引出波幅在 50 μV 以上的运动诱发电位,则认为该刺激强度是 RMT,它反映了中枢运动神经的兴奋性。本试验采用 90%RMT 的强度进行干预。试验时借助了 MRI 的导航定位,精确地把握干预位置。
1.4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试验数据采集设备为 64 导高密度 EEG 信号检测仪(BrainCap 标准型,德国),导联方法采用国际 10–20 系统,记录软件采用 Brain Products 公司研发的 Vision Recorder 系统;数据预处理采用 Vision Analyzer 系统。由于采集过程中 FP1、FP2、TP9、TP10 电极阻抗过大,所以试验数据分析中选用了 58 个电极位置,EEG 信号采样频率为 1 000 Hz,电极和头皮接触电阻小于 20 kΩ。预处理步骤包括带通滤波(0.05~80 Hz)、邻近导联平均(去掉不好的导联)、去眼电信号干扰、数据分段(刺激前 200 ms 到刺激后 1 000 ms 为一段)、基线校正(前 200 ms 数据视为基线)、伪迹校正(剔除大于 100 μV 的数据段)等,最后将数据导出作后续处理。
考虑到数据的鲁棒性和合理性[17],本文在后续处理中选取刺激后 800 ms 的 EEG 数据作为原始数据。首先进行事件相关功率谱分析,选取相应的频段。然后为了探索 cTBS 刺激下的大脑情绪加工的时变信息,本研究将数据进行分窗处理,从刺激时刻开始每 200 ms 取一个窗,以 50 ms 为步长选取第二个窗,即 1~200 ms 为第一个窗,50~250 ms 为第二个窗,依此类推直到包含全部数据,共 13 个窗。因此,刺激后 800 ms 的数据共分成 13 个数据段。试验获取相应频段的数据采用小波分解方法,将预处理后的 EEG 信号分为 δ(1~4 Hz),θ(4~8 Hz),α(8~12 Hz),β(12~30 Hz),低 γ(30~50 Hz),高 γ(50~80 Hz)6 个频段,选取 db5 作为“母小波”,分解级数为 7。
1.5 事件相关功率谱分析
研究证实,运动、感知和认知的信息加工,会引起 EEG 信号的变化,形成事件相关去同步化(event-related desynchronization,ERD)和同步化(event-related synchronization,ERS),通过事件相关功率谱(event-related spectral perturbation,ERSP)可以衡量 ERD/ERS 的变化[18]。本文使用 db5 小波的复指数形式计算谱功率。
定义小波的复指数的解析式为:

 ,式中
,式中
 代表窗函数。则信号
代表窗函数。则信号
 的时频分析定义为:
的时频分析定义为:
 |
f 和 t 分别代表频率和时间。
对每段 EEG 数据进行小波变换,对变换后的所有数据段进行平均后取绝对值,即定义为平均 ERSP:
 |
最后,本研究对平均 ERSP 做基线矫正,即通过逐点减去前 200 ms 的 ERSP,得到相对基线的 ERSP。
1.6 脑功能网络分析
基于 EEG 信号研究特定频带内的脑网络时,采用相位同步来量化各通道信号之间的关系比较合适[19]。脑功能分析的第一步是构建网络,本文采用相位同步法构建基于多通道 EEG 信号的大脑网络。它是通过希尔伯特(Hilbert)变换把窄带的波形信号分解成幅度部分和相位部分,进而分析两信号间的相位关系[14]。如对于 EEG 信号采集电极 A 和 B,若解析信号的相位差满足:
 |
那么就称两信号相位同步(通常取 p=q=1)。信号间的相位同步水平可以用相位同步指数来刻画,定义相位同步指数为 r,如式(4)所示。
 |
其中,M 为采样点数。则 r 值在[0,1]之间,值为 1 表示相位完全同步;值为 0 表示相位完全不同步,代表了网络的连接强度。最终可以得到 58×58 的矩阵。
在确定网络连接强度之后,计算网络成本。网络成本(Cost)也就是网络的密度,即网络的连接边数与最大可能连接边数的比,如式(5)所示。式中,N 代表网络中节点(EEG 通道)总数,K 代表网络中存在的连接边数。
 |
本研究选取网络成本范围为[0.02,0.5][20],步长为 0.02,在每一个确定的网络成本下根据公式(5)计算 K 值,由 K 值确定阈值(连接强度),对相位同步矩阵转化为加权无向网络,即仅当矩阵中元素大于等于阈值时保留相应的值,否则为 0。在每个网络成本下建立加权网络后,计算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值。另外本文在建立每个加权网络的同时构建相应的随机网络和规则网络,该随机网络和规则网络具有与真实网络相同的节点数和有效连接边(N=58,K 是不同密度下有效连接边数),并计算其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值。本文构建网络借助 MATLAB 2011BCT 工具包中的功能函数对构建网络进行分析。网络分析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3
基于 EEG 信号的脑功能网络分析流程
Figure3.
Analysis process of brain function network based on EEG signals
图3
基于 EEG 信号的脑功能网络分析流程
Figure3.
Analysis process of brain function network based on EEG signals
1.7 网络效率分析
在网络的连通图中,Li,j 定义为最短路径长度即连接 i 节点和 j 节点的所有路径中,连接边数的最小值。两节点之间的连接效率与最短路径长度成反比。网络的全局效率 Eglobal,代表了整个网络的信息交换能力,定义为
 |
全局效率值越大,表示信息或能量等在该网络上进行交换时所需的代价越小[19]。
局部效率近似于聚类系数,反映了对一个特定节点 i 的最邻近间信息交换能力。定义局部效率 Elocal 为:
 |
式中,NGi 表示子网络 Gi 中节点的个数。平均局部效率是子网络中每个节点效率的平均值。网络的成本效率为网络的全局效率与网络的成本之差。
 |
网络的成本效率随着网络的改变而改变。
本文在分析单一网络成本下的局部特征时,又将大脑划分为左、右半球两个脑区和左/右额区,左/右颞区,左/右顶区和左/右枕区八个脑区。每个脑区的所有电极的局部效率均值作为该区域的局部效率值。如图 4 所示,中线左边为左半球,从上到下,从左至右分别是左额/颞/顶/枕,中线右边则为相应的右半球脑区。对不同情绪下的局部效率值做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组间因数为 cTBS(干预前/干预后)、半球(左/右)和脑区(额/颞/顶/枕)。
 图4
各个脑区选取分布图
Figure4.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brain regions selected
图4
各个脑区选取分布图
Figure4.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brain regions selected
1.8 统计分析
本试验数据都通过 SPSS 16.0 中的一般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GLM)完成统计分析。对各项统计检测值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内因素为情绪(正性/负性/中性)和 cTBS 干预(干预前/干预后),无组间因素。若 cTBS 与情绪之间(cTBS & 情绪)存在交互效应,则进一步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对于统计分析结果的描述,如果检验 P<0.05,则认为存在主效应或交互效应。
2 结果
2.1 事件相关功率谱
如图 5 所示,为包括 cTBS 干预前和干预后,以及正、中、负性三种情绪刺激在内的 ERSP 时频图。可以看出:在情绪加工过程中,频带在 40 Hz 以内出现活跃状态,并且在 β 频带内 100~300 ms 脑内活动明显增强;然而,cTBS 干预后抑制了大脑的活动,脑内能量明显降低,尤其是负性情绪的变化非常明显。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 100~300 ms 内 β 频段内的大脑网络特性。
 图5
cTBS 干预前后三种情绪刺激下 ERSP 图
Figure5.
ERSP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under three kinds of emotional stimuli
图5
cTBS 干预前后三种情绪刺激下 ERSP 图
Figure5.
ERSP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under three kinds of emotional stimuli
2.2 情绪加工网络
本文采用相位同步法量化 EEG 通道间的关系,建立多网络密度下的情绪加工脑功能网络,进而进行复杂网络分析。如图 6 所示为 cTBS 干预前/后,三种情绪刺激下 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的相位同步矩阵。其中矩阵大小 58×58,每个元素表示相位同步指数,对角线元素为 0。横、纵坐标代表相应的导联,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对应的是大脑从前到后的导联分布。
 图6
β 频段 100~300 ms 时间窗的相位同步矩阵
Figure6.
100~300 ms Phase synchronization matrix of β band
图6
β 频段 100~300 ms 时间窗的相位同步矩阵
Figure6.
100~300 ms Phase synchronization matrix of β band
对 β 频段在 100~300 ms 内的全局相位同步值统计分析发现,cTBS 存在主效应趋势(F=4.529,P=0.062)以及 cTBS 与情绪之间存在着交互效应趋势(F=3.438,P=0.059)。又通过进一步地简单效应分析得到:① cTBS 干预前三种情绪两两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TBS 干预后,正性情绪与中性情绪(F=7.984,P=0.020)以及与负性情绪(F=6.222,P=0.034)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 中性情绪刺激下 cTBS 干预后相位同步值增加(F=7.918,P=0.020);负性情绪刺激下 cTBS 干预后相位同步值具有增加的趋势(F=3.411,P=0.098);而正性情绪刺激下 cTBS 干预前后的全局相位同步值无明显差异,如图 7 所示。
 图7
cTBS 干预前后 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平均全局相位同步值 *P<0.05
Figure7.
100~300 ms Phase synchronization average value of β band under the positive,neutral or negative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P<0.05
图7
cTBS 干预前后 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平均全局相位同步值 *P<0.05
Figure7.
100~300 ms Phase synchronization average value of β band under the positive,neutral or negative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P<0.05
试验中,将基于 EEG 信号构建的情绪加工网络与相应的随机网络和规则网络进行对比。结果发现:情绪加工网络在网络密度(0.24,0.5)内,全局效率低于随机网络而高于规则网络,其局部效率则高于随机网络而低于规则网络,具有小世界特性。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随网络密度变化的曲线如图 8 所示,第一列为正性、中性和负性三种情绪加工网络的全局效率曲线,第二列为对应的局部网络曲线。我们再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局部效率在密度(0.24,0.36)下都有 cTBS 主效应或主效应趋势,全局效率在(0.24,0.5)区间内无任何差异。另外,没有情绪主效应或 cTBS 与情绪之间的交互效应存在。由小世界网络特性可知,网络密度在(0.24,0.36)内,cTBS 干预后情绪加工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增强,如表 1 所示。
 图8
随机和规则网络及 cTBS 干预前后的情绪加工网络的全局和局部效率曲线图
Figure8.
Global and local efficiency curve of random,lattice or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ing of emotion
图8
随机和规则网络及 cTBS 干预前后的情绪加工网络的全局和局部效率曲线图
Figure8.
Global and local efficiency curve of random,lattice or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in the processing of emotion
2.3 单一网络密度下的网络局部特征
网络密度也即是网络的成本,网络的成本效率可以说明是全局网络与成本的差。β 频段 100~300 ms 时间窗内各因数下的成本-效率的关系如图 9 所示,可以看出,成本效率在较低成本区间内逐渐增大,达到一个最大值,然后成下降趋势,整个曲线犹如抛物线。cTBS 干预前、后,正、中、负性三种情绪加工网络的最大成本效率对应的成本在 0.28 左右。此时,网络具有最“经济”的模式。
 图9
cTBS 干预前后,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成本效率曲线图
Figure9.
Cost efficiency curve of the 100~300 ms time window of β band in three kinds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图9
cTBS 干预前后,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成本效率曲线图
Figure9.
Cost efficiency curve of the 100~300 ms time window of β band in three kinds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针对最“经济”模式下(网络密度 0.28)的脑网络,我们进一步选择了对大脑区域的局部效率进行分析。局部效率的脑地形图如图 10 所示。在 100~300 ms 时间窗内,正性情绪刺激下,干预后各个脑区的局部效率值高于干预前。中性情绪刺激下,干预后左半球各个脑区的局部效率值都高于干预前,右半球脑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且在 cTBS 干预后,左额、左颞、左顶区的局部效率值都高于右侧对应的脑区,枕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负性情绪刺激下,同样显示左半球各个脑区干预后的局部效率值高于干预前,干预后左半球的局部效率值高于右半球。
 图10
cTBS 干预前后 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局部效率的脑地形图
Figure10.
Brain topographic map of the local efficiency of the 100~300 ms time window of β band in three kinds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图10
cTBS 干预前后 β 频带 100~300 ms 时间窗内三种情绪的局部效率的脑地形图
Figure10.
Brain topographic map of the local efficiency of the 100~300 ms time window of β band in three kinds of emo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cTBS intervention
3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 cTBS 干预下 EEG 信号特性,探究左侧 DLPFC 在情绪加工脑网络的作用。结果表明,ERSP 在 cTBS 干预后 100~300 ms 与干预前相比出现增强,尤其是 β 频带范围内激活明显。干预后,正性情绪刺激下的 EEG 信号全局相位同步值和中性、负性情绪刺激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一定的网络成本范围内,情绪加工网络的全局效率及局部效率介于随机网络和规则网络之间,具有小世界特性,而且,在网络成本区间(0.24,0.36)内,cTBS 干预后,脑功能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增强。
很多研究都已经表明,大脑前额在情绪加工过程中占据着重要作用[2-3]。神经影像学的研究表明左侧 DLPFC 涉及到负性情绪的判别[6]。如前所述,有研究者发现与正常人相比,轻度抑郁症患者做情绪性别识别任务尤其是在负性情绪刺激下的情绪性别识别任务时,左侧 DLPFC 活跃性降低[7]。本试验通过采用 cTBS 技术抑制左侧 DLPFC 的活动后,发现相比于正性和中性情绪刺激,负性情绪刺激下情绪面孔性别识别任务的 ERSP 降低更明显。进一步证明了左侧 DLPFC 在负性情绪判别中的特殊作用。
EEG 信号相位同步值分析结果显示,cTBS 干预后与干预前相比,情绪加工脑网络具有高的全局相位同步值。研究发现大脑信息整合和处理的潜在机制是各神经网络的同步性震荡引起的,部分难以治愈的神经性疾病由大脑整体和局部整合过程的不足和异常造成[21]。而 EEG 信号反映的是神经元集群突触后电位的累积效应,其相位同步能反应大脑神经电活动的整合作用,高的相位同步可能对应着大脑大范围的整合[22],代表大脑具有很高的信息整合能力。另外,研究证明 DLPFC 与其他区域的紧密连接以及皮下层区域间的非直接联系参与了情绪认知信息加工,侧前额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LPFC)更涉及到高阶的认知处理[23]。本研究中 DLPFC 的活动受到抑制,打乱了原有的功能连接,为了完成情绪面孔性别识别任务,必须重新调动和整合各参与脑区的资源,最终导致网络的全局相位同步值升高。
很多研究者证实了人脑网络存在着小世界特性[20],并指出小世界网络具有较小的特征路径长度和较大的聚类系数。基于解剖学的研究也发现了大脑具有短的轴突连接或者低的代谢消耗,即大脑可以选择在某些范围内紧密连接,达到较为高效的“经济”模式,以降低能量消耗[24]。这意味着大脑具有更高的全局和局部效率。本研究中,使用网络成本系列值计算全局效率和局部效率值,得到情绪加工网络小世界特性区间为(0.24,0.5)。已有研究利用神经影像技术数据建立大脑网络,证明功能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在中低成本区间内[25-26]。cTBS 干预左侧 DLPFC,抑制了该区域大脑的活动,可能同时促进了对侧区域的皮层兴奋[27-28]。因此,干预后特定局域内功能网络发生改变,使得局部范围的连接更紧密,从而具有较高的局部效率。
当网络的成本效率达到峰值,如图 9 所示,即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高的效率时,此时“经济”的小世界网络特性体现最为明显。本研究中,网络成本为 0.28 时,成本效率达到峰值,表明此时的网络最“经济”。当网络成本效率达到最大时,我们发现干预后的左半球局部效率有所增加,这可能与干预后引起局部范围的连接紧密有关。
本研究揭示了 cTBS 干预后情绪加工网络小世界特性增强,证明了当成本效率在中低范围内,具有特异的网络性质,证明了左侧 DLPFC 活跃性改变对情绪加工脑网络的影响。本文的试验是对情绪加工网络机制的初步探索,为以后的情绪脑功能网络研究提供了参考,未来的工作应从网络分析方法中多个角度更全面地分析情绪脑功能网络特征,进一步研究情绪加工网络机制。